卡瓦拉泽 | 鸟
作者:卡瓦拉泽
来源:西藏文学
时间:2025-08-13 08:55:19
点击数:
一
我躺在床上,睁开双眼,突然听见地板吱吱呀呀地响起来——有人来了。那熟悉的脚步声一定是扎西。可门锁明明已经换了,他怎么会进来?我想逃,可是无处可逃,只好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我死死地盯着卧室门,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的嘴碰到了手上的戒指,刺骨的冰凉透过厚厚的嘴唇和牙齿好像传到了整个头骨。我抬眼仿佛看见了半个黑影站在门边,手里拎着什么东西。世界突然安静了。
我猛地睁开眼,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离婚以后,我总是做一些很奇怪的梦,比如梦见自己变成长不大的小孩、变成扎西的衣服、变成扎西的样子,还常常梦见和他接吻后,他又突然拿着书本砸向我。
不过现实生活里砸向我的常是他刚喝空的酒瓶。那天喝醉的扎西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嘴里在嘟囔着什么,可能是尼采、加缪,他就爱谈论这些,好像认识这些人能让他一夜跃升到上流阶层似的。我不在意他那些忧郁的人生思考,只觉得酒后的男人都很臭,我不想让他上我的床。
他的手机扔在一旁,正不停震动。鬼使神差地,我试了几次密码,打开了他的手机,对话框里赤裸的对话像是把两个人都脱光了扔在我的眼前一般,我浑身战栗,双手忍不住颤抖。我向对面发去消息:“你是谁?”
对面迟迟没有回复,但我看见聊天框的上方不停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我的呼吸急促,胃里好像在翻江倒海。我快要吐出来了,但明明我晚上没有吃东西。我看了扎西一眼,他微睁着迷离的双眼,并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
对面始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过了五分钟,那人却打来了电话。我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愤怒说:“喂。” 我的声音沙哑着说:“说话!” 我不停颤抖。对面沉默了一会儿,挂掉了电话。我疯了似的把扎西从地板上拽起来,抓住他的衣领咆哮,眼珠子像是要掉出来一样瞪着他。可他却和对面一样沉默。
我扔下他,拨回了电话,扎西盯着手机屏幕的眼睛突然变圆,想将手机从我手中抢走。
可是他喝的太多了,以至于身子瘫软,坐不起来。他只是靠在墙上,双手无力地乱抓。我盯着他猩红的双眼,拿着手机走到另一个角落里,他怒吼一声,抓起手边的空瓶子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走来,把酒瓶砸向我。
那天晚上我就把扎西赶出了家门,尽管他马上向我求饶,好像刚才砸我的时候是鬼上身了一般。他跪在家门口,我把他的一切都扔了出去,不管冬夜的风有多么刺骨。院子里的人们都被我们的争执声吵醒,不知是房间里黄澄澄的灯光还是头顶明晃晃的月光,我只觉得那么刺眼,天旋地转。
从那以后,我常做噩梦,所以这次也并不觉得奇怪了。我醒来后摇摇脑袋,撑着床沿慢慢站起来。拉开窗帘,远处是被雨水滋养得毛茸茸、绿油油的山,原来已经过去半年了,我想。
雨是突然下起来的,比平日里更暴烈,听起来街上的行人也更吵闹。我趴在窗边,低头看着路上花花绿绿的伞,它们好像有生命的拼图一样严丝合缝地拥挤着,伞下的人们看似热烈地碰撞,其实只是在互相推搡,并未前行。
我关上了窗户,朝沙发走去。
这时,我听见身后响起了有节奏的叩击声,转身看见一只鸟在啄窗玻璃。或许是我家窗台总撒着一些大米、青稞的缘故,飞过的野鸟常会在我这里停留一阵。于是我又折返回去。它淋湿了,灰色的羽毛居然泛起了钴蓝色的光泽,像是唐卡用的矿石颜料,我以为这是只野生的小鸟在不慎打翻了哪位画师的颜料后匆忙逃出。但细看又不太像,它应该是被人精心饲养的,因为它看起来并不怕人,只是歪着头看我。
但不知为何,我从它的眼里读出了傲慢,好像笃定我会让它进屋似的。
我打开窗伸出手,它随即跳上指间。细细观察它,那雍容华贵的钴蓝色好像消失了一般,我又看见它长长的尾羽在颤抖,应该是有些害怕我,它不像在窗外时那么傲慢了。
“还以为是什么神鸟呢。”我轻笑。我抽出一张卫生纸,擦拭它身上的雨珠,看见它脚踝处有细小的伤痕,又拿来一些新鲜的糌粑喂它。
“你从哪里来?”我又问,像是在自言自语。
它不回答,只是轻轻啄我手上的戒指,像在评判它的成色。戒指是扎西送的,我曾想过把这枚戒指丢掉,但又纠结了许久,或许是为了给自己长时间的沉没成本留个念想。
它脚踝上的伤口本来就浅,所以几天后很快好了,我便想着把它放走,但它面对着大开的窗户无动于衷,只是轻轻啄啄我的手背和那枚戒指,甚至还飞到我的肩膀上,歪头看我后又蹭一蹭我的脸颊,像只小猫,我明明每天都蓬头垢面,可是从它眼里居然看出了欣赏。那时我的目光一定怜爱起来了,心中生出了舍不得它的感觉,就默许它留下了。
我给这只小鸟起名“琼”,因为第一眼见它时羽翼上有一抹蓝色,像是琼鸟。尽管后来那抹蓝色时有时无,但很神奇,因为它的到来,我睡了许多安稳的觉。
夏天开始,我的梦不再恐怖,也不再梦见扎西。梦里常常都有琼站在我的肩膀上,每当这种时候,它的羽翼都会变得更加美丽,钴蓝色上浮现出细小金纹。在梦里,我和琼相视,如我所愿,所有的时钟都停摆了,四处闪着霓虹灯的光芒。
我摘下了戒指,送给琼当玩具。
二
我没有鸟笼,所以琼有时会飞出去,但总会回来,我从不管它。琼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我分不清是不是幻觉,它的羽毛上好像真的出现了细小的金纹,像梦里一样。但我家里却越来越乱,四处散落着有关它的一切。琼从外面飞回来的时候,常常衔着亮片或纽扣,像是礼物。我摊开手掌,它会轻轻放下那些小玩意儿,然后用尾羽扫过我的掌心,带着煨桑的气味。能看出它是从八廓街拍照的游客身上“偷”来的。这样的次数多了后,我发现它好像很希望我戴上“礼物”,因为它不再只满足于把小饰品放在我的手心,而是直接会放在我的头发上、衣服上,以及任何它想放的地方。
我向琼表达过自己的不喜欢,也总想让它还回去。但它无动于衷,第二天又衔着些新东西回来。有时它会让我想起巧言令色的扎西,我只好安慰自己,琼和扎西不一样,它只是听不懂人话罢了,于是一般也默许这些行为。不过它的品味我实在是不敢恭维,那些假绿松石耳坠或是假珊瑚手串其实都还好,但它喜欢那些夸张的、像它羽毛一样的廉价饰品。
我渐渐意识到,琼好像在按自己的喜好打扮我。每当我任它摆弄时,它总会兴奋地在我头顶盘旋一阵子,然后昂首在窗户前等待着什么,直到一群灰鸟飞过。有时我会产生一种我才是琼的宠物或是时尚配件的错觉,供它向同类炫耀。
直到有一次,琼带回来一个毛茸茸的狐狸耳发夹,是我最不喜欢的那种。它站在我头上,侧身轻轻啄我的脸颊。我明白它的意思是让我戴上,但我不想,不过我的反抗只是不回应,继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玩手机,我这不明显的反抗让它又以为是某种默许。
琼便开始自己行动,它抓住我的头发,在我的头上颠三倒四,弄得像它的老巢。我抬头看了它一眼以示警告,但它并未停下来。突然,我感受到了它尖锐的爪子或是嘴在扯我的头皮,疼痛感很快驱使我挥起双手。它扇扇翅膀飞到一边,爪子上还带着几根我的头发,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
“真会演戏。” 我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好像原谅了它,想要打它的手只是轻轻拍了拍它,因为总觉得它真的听不懂人话。
我真是太擅长给它找借口了,给人也是。
扎西被我赶走后,还真没有再出现在家里了。除了预约办离婚登记和办手续那天,其他时间他从不联系我。和他刚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很有耐心地为我做一切事情。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是我的问题吗?
尽管我不再做可怕的梦,但白天我仍旧像一滩烂泥躺在床上,浑浑噩噩,只会为了琼把客厅的窗户打开,自己睡的房间紧闭窗户,窗帘也不再拉开。莫拉们担心我,常来给我送吃的,听见敲门声后我才会起床,打开门看见她们布满皱纹的双手捧着一盒风干牛肉,干瘪的手皮皱起来,藏着一些干肉丝,她们应该才刚吃完。我看着她们浑浊的眼白想,幸好,她们应该看不清我现在的丑状吧。
每到晚上我都在哭泣,可能把前半生的眼泪都哭干了。有时居然还期待他再回来,想着会不会是当时把他的东西扔出门的时候,忘记把钥匙丢给他了;有时担心他没地方住,没有人听他那些无聊的哲学思考,喝了酒之后会不会睡不好,他如果回来,我不会再让他去睡冰凉的地板了,我会煮好醒酒汤等他,等他回家后把他扶上床。他好可怜,我想得快要哭了。转眼我又想,他一定找到了真爱,她一定会好好对他的,既然这样,我也应该放手,爱是我给予出去的,本就不应该奢求回报。
但很快我又会强制自己结束这种想象,起床去逗一逗琼,如果它在的话。这样我的心情会好很多,琼有时喜欢飞到我手里,用它的体温为我取暖,很奇怪,即使刚从暖和的被窝里出来,我的手仍像冰块一样凉。
那次“打”了琼之后,它稍微收敛了一段时日。可时间不长,它又开始把假珊瑚手串扔到我头上,我抓住它的爪子,握住它的嘴:“这次换我来画。” 我打开口红,在它肚子那里乱画一通。
三
冬天到了,琼出去的次数减少了,寒冷的天气让我把客厅的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天晚上,一声闷响惊醒了我:一只铁灰色的鸟坠在窗台上,和琼长得很像,只是看起来比琼更圆润一些,尾羽也没有那么长,应该是只雌鸟。我推开窗想救它,它却猛地振翅,爪子在我的虎口划出一道很深的血痕后就飞走了。
那一瞬间,我看见它脚踝上有褪色的脚环,与当时琼受伤的位置一致,脑子里一个奇怪的念头一闪而过——它们应当是同一户人家里逃出的鸟。但我没有继续多想,只顾翻箱倒柜找出酒精和棉片给自己消毒。琼应该在一旁立了很久,我转头看它时,它的羽毛已经变得蓬乱。
我觉得它被那只雌鸟吓到了,我也是,于是很快清理干净雌鸟撞窗的痕迹。
第二天,我听见楼下莫拉在喊我,仔细一听是她们在问要不要新炸的卡塞,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又好像听见咋舌的声音。我突然害怕她们发现了昨晚的什么事,误以为我精神失常,甚至虐待了鸟,于是慌张地跑到窗边,看了看昨晚的痕迹,那里被我清理得确实很干净,这才打开窗户对着莫拉们笑着说:“肯定要呀。”
她们很开心,说很久没见我笑了。罗萨要来了,新的一年会是新的开始。
一切确实变得不一样了。
我的笑容变多了,也开始走出家门。琼也是,只是感觉它变得不好了。
最近几日,尽管外面寒风凛冽,琼外出的次数开始变多,它总是趁我没关窗时偷飞出去,夜晚又像我初遇它时那样,用嘴敲敲窗户。不过每次回来,它的羽毛都乱糟糟的,我担心它是不是被冻着了或者生了什么病,想让它在家里休息一段时日不要出门,但又想着它本就是属于自然的生灵,何必把它困在我这间房里,便又默许了。
可一段时间后,琼看起来仍然没有好转,每天都能感觉到它掉了很多羽毛。我又担心,和我在一起生活那么久,琼应该已经算家养的鸟了吧,在外面会被其他野鸟欺负的。
我开始好奇它都去了哪里,那段时间我起得很早,看着它飞走后才出门。不出所料,它飞去的总是同一个方向。于是我想给琼戴上追踪器,尝试了很多次,从未成功过,它总是在我抓住它的时候突然发狂,将我啄伤,好像明白我要做什么似的,我的手上也多了许多道它留下的伤痕,就像扎西那次朝我扔酒瓶一样。
琼将我啄伤后,我又开始睡不安稳,梦里我发现琼身上忽隐忽现的蓝色只是楼下霓虹招牌的反射,它悬在我头顶,发出凄厉可怕的叫声,瞪着血红的眼睛朝我扑来,它的爪子狠狠地在我背上划过,我挠不到伤口,但感觉到了钻心的疼痛,我盯着满手的鲜血时,它突然用那灰黑色的巨大翅膀在我的脸上猛扇了一巴掌,我头晕目眩,倒在地上,仿佛突然失明了一样。还没来得及看清,又感受到它那刀锋般的喙在我身上啄了无数个洞,那一瞬间,它又变成了扎西,那张巨大的、狰狞的脸朝我靠近,在我耳边低语:“你早该明白,你离不开我。”等我能看清时,又看见琼的嘴尖停在离我眼球两厘米的地方。
我惊醒,看着窗户玻璃反射的街边的霓虹灯,又看看站在衣柜上的琼,它看起来乱糟糟的,睡着了。
再次开始做噩梦又能怎样呢,生活也只能这么随意地过下去了。琼在家里时总是蔫巴的,直到有一天,回家路上我看见琼和一只鸟盘旋在天空中,像是那天撞窗的雌鸟,琼和在家里的样子很不一样,它的翅膀不停扇动,一会儿落到这根树枝上,一会儿又飞过水面,一会儿又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地前行,甚至在它们的身后,我还看见了几只雏鸟。
原来它们真的认识得比我早,我思考了一会儿,决定将琼放走。又想起自己想给它装上追踪器的想法,很可笑,怪不得它要反抗。
我上楼,却发现琼在家里,萎靡不振的样子和前几日并无区别。窗户半掩着,琼应该飞不出去。我又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看错了,天空中的两只鸟其实并不是琼和那只雌鸟。但我仍决定放琼走,它本就不应该生活在只有人类的环境里。或许放走它,我就不会再做有关它的噩梦了。
放生那日,我攥着琼的爪子将它扔出窗外,它又开始发狂,甚至啄我的锁骨,我一手摁住它,一手将它从我的身上扔出,莫拉们在楼下张大嘴看着,琼在空中盘旋,发出刺耳的鸣叫,像我梦中梦到的它一样。
琼很快飞走了。我关上了窗户。
夜晚很快来临,窗户那里又响起了熟悉的声音,带着理所当然的蛮横。我看着窗户外的琼,突然意识到,我本就从未困住过琼,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当成我的宠物豢养。
我打开窗户,它飞了进来。
是它自己要回来。
四
琼回来后,我对它冷淡了许多。我想让它远离我的世界,但好像又无法将它完全赶走。它总是在深夜的某个时刻出现在窗边,我却又总是鬼使神差地打开窗户让它进来。它每天自己飞进飞出,好像默认了我的冷淡,也不再发狂和啄伤我,它真的很像我的一位房客。敲门声响起时,我正在往我的伤口处涂抹药膏。透过猫眼,我心里一惊,一年不见,扎西的脸变得像被雨水泡发的馒头一样松垮地坠在肩头。路过的莫拉跟他打了打招呼,我看见他抬手摸了摸鼻子,手上仍然戴着那枚戒指,“哼。” 我冷笑一声,打开了门。离婚这么久,他从未联系过我,只在我的噩梦里出现。但这人见我并没有任何陌生感,谄媚地笑着,一上来就动手动脚,好像他的时钟在离婚之前停摆了一样,我抬起手推开他,坐到离他很远的角落里。
琼飞回来了,它看见家里的陌生男人觉得奇怪,飞到我手边朝我示好,像最开始那样。但我挪了挪身子,没有心情理它。
我还是答应扎西去吃一顿饭,他坐在对面,居然主动问起我这半年的情况,我还没回答,他起身抽开我身旁的椅子,坐了下来,把腿搭在我的腿上,像小猫一样在我身上蹭来蹭去,尽管我说了我刚吃完小龙虾,虾壳掉在身上染脏了衣袖,他也毫不在意。以前扎西对我的生活丝毫不关心,只会不停地讲他自己,让我做一个沉默的倾听者。但我说了一会儿近况,就意识到情况其实并没有好转,因为扎西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尼采,手指在我膝盖上画圈。我仍然听不下去他这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感觉在拿书本砸我的头。
我走神了,突然想起琼,它还没有啄伤我的时候,有时喜欢飞到我手里,用它的体温为我取暖。在梦里琼站在我的肩膀上,和我相视,时间停止,它的羽翼好美丽,钴蓝色上浮现出细小金纹。
它好美啊。它应该在家里等我,也许它现在正急得团团转。
我起身就走,留下扎西一个人在那里。
到家后,琼朝我飞来,我第一反应还是以为它要来啄我,但好像并不是。尽管如此,我又恢复了对琼的冷淡,径直走向卧室,关门睡觉去了。
第二天醒来,看见它仍然乱糟糟的羽毛,我突然又心软了起来。它发出呜咽声,不像健康的鸟鸣,看见它期盼的眼神,我会害怕,害怕自己养不好它,我觉得所有的事物只要和我在一起就会变得不好。走到一边,我看到它专属的鸟食罐里空空如也,于是往里倒满了青稞和糌粑。
我又开始细心照料它了,说是细心,其实也只是不停朝它的鸟食罐里添加新鲜的食物,常常祈祷,希望佛祖保佑它快快好起来。可是奇怪,它看起来没有一点好转。
尽管琼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但它又开始频繁地飞出家去,不知道飞向哪里。上次的经验让我不再关心它的去向,我相信它一定会回来。但这次我发现我每天都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可又害怕这等待成为惯性,从而让我的心再一次裂开。
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为我从八廓街衔来那些奇怪的礼物了,看起来它的心情很差。我想安抚琼,可一触碰到它,它又开始浑身战栗,开始在家中四处乱飞,翅膀扇翻了我的花瓶,扇到了我的脸,好像我才是那个让它受伤的人。
有一天,我居然梦见了那只灰色的撞窗雌鸟,它和琼像是在半空中厮打,紧接着琼又飞回我家,楚楚可怜。
仍然不是一个好觉。
可是第二天,我真的看见了那只撞窗的雌鸟。让我怀疑自己昨晚的梦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而且它真的受伤了,就像真的和琼厮打了一样。我想喂它些吃的,于是,我用指尖抓了些撒在窗台上的糌粑,可雌鸟却退后三步。我又把糌粑放在我的掌心,它纹丝不动,瞳孔在阳光下缩成竖线,像面镜子,映出我举着掌心的姿势。
它飞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总能看见它站在窗台上向屋里望,不知道是偷窥我还是偷窥琼。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可有一天,它叼来草药放在窗台,虽然我早都好了,但它好像知道我曾因为琼受过伤。我甚至觉得它用一种悲悯的眼神看我,像是我被琼骗了还不自知。
五
琼已经连续三天没回家了,我的等待真的成了惯性。我不停告诉自己,野鸟本就该自由。可我还是在窗台上摆了很多种不同的谷物。睡不着时,我凌晨三点去给它的鸟食罐加水和青稞,月光把鸟食罐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扎西被我赶出家门那天的月光。我安慰自己只是怕它饿死,久久站在窗台边,直到发现自己在对着空窗台说话。我叹了口气,准备关上窗时,发现了几根琼的羽毛,竟然一丝一毫的蓝色都没有,我又拿到窗边细细端详,才发现真的是霓虹灯的反射。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
在那之后,雌鸟不再来“偷窥”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琼死了,过了两天雌鸟也撞窗死在了我家的窗台上,莫拉们站在院子里朝着我家的方向骂我,她们的表情像那天我把扎西赶走时一样,我出门遇见她们时,她们都把头别过去。
我又被吓醒了,但仍觉得心慌,只好跑去寺庙,听见法号声和僧侣的吟诵声,我便心安了,看见佛龛上燃烧的酥油灯,我开始感激,抬头看见黑夜里隐约飘过的桑烟和明亮的星辰,我觉得宁静。
但我走神了,想不起自己来寺庙的初衷是什么。我满脑子都是,那颗星星叫什么?看见游客们拿着相机不停拍摄跳动的火苗,屋顶上的古修啦也在拿着手机录地面上的信众。燃尽的酥油灯被古修啦们用哈达擦净后放进塑料桶里,碰撞的声音让我想起啤酒瓶。古修啦不和人纠缠,怎么会有大智慧?灯倒下了怎么办?着火了怎么办?我被自己这些突如其来的想法吓到了,这是大不敬,我想。
一位古修啦突然对我说:“你和不该在一起的东西在一起。”
我愣住,还想继续追问时,他已经走远。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明明我早已和扎西切断了联系。只好开始每晚念经,我起初觉得绕口,常常嘴瓢,后来念习惯了,在顺畅的诵经声中,我的脑海一遍又一遍重演那些让我痛苦的梦魇,一会儿是扎西,一会儿是琼,于是我念着念着哭了。但过了很久,我仍并不明白经文想要告诉我什么。
过了半个月,琼居然回来了。
它依旧理所当然地敲窗户,并没有任何陌生感,好像这半个月的时间静止了一般。我某一瞬间在它脸上看见了那次扎西谄媚的笑容,突然感觉如果打开窗户,琼会变成扎西,一上来就对我动手动脚。
我转身走向了我的沙发,当作没有听见,念起了经文。
琼不再敲窗户,这次也没再回来,它应该真的回到它的鸟类世界里去了吧。
门窗真的很好,隔绝了我和很多人,和鸟。
扎西后来来找过我几次,但我再也没有给他开过门。窗户也是,我很久没有大开过了,春天到了,拉萨的沙尘天气太严重了。
有一天我在河堤上散步,看见一只死鸟躺在草丛中,它的脖子被生生咬断,和琼很像,周边散落着像雌鸟身上颜色的羽毛。我不相信是琼,可看到旁边沾着干涸血渍的戒指时才不再怀疑,那是我的戒指。
昨晚我又梦见我变成了一只鸟,我好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梦了。我的羽毛光鲜亮丽,我在梦里窃喜,幸好,我长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模样。但是我的主人从不让我展示自己的羽毛,他们把我关在笼子里,每天都对着我喋喋不休,好像希望我能像鹦鹉一样说话。我趁他们给我换吃食的时候,飞了出去,我很兴奋,感觉自己飞了很久,却突然被一双大手握住,我惊恐地看向四周,原来我只是飞到了主人家的二楼,房子里还有无数关着的窗户,我看着那些玻璃,好像快要死去。
又一年夏天到了,我醒来,洞开家里所有门窗。
相关推荐
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媒协会成立
近日,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媒协会在西昌市成立。四川民族杂志社社长、总编马飞当选为协会会长,四川民族杂志社、四川广播电视台、康巴卫视台、凉山日报社、阿坝日报社、甘孜日报社等6家单位为协会会员。 6家单位通过了四川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媒协会...
2011-10-08 编辑:admin 19813多布杰获全国锦标赛男子5000米冠军
近日,在重庆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的2021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资格赛男子5000米决赛中,西藏拉萨城投队选手多布杰以14分03秒52的成绩获得冠军。
2021-06-29 编辑:青阳卓玛 23234阿坝州六寨女王山神节
三位参赛选手跑到终点 近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安羌乡“六寨女王”山神节期间,煨桑、拜神、建“拉最”(藏区供奉彩箭和经幡的台子)与山歌、民歌,锅庄舞、现代舞融为一体,让当地群众体验到了不一样的藏族宗教、民俗文化活动。 一位参赛选...
2016-03-15 编辑:admin 24332阿坝州红原打造大草原国家公园
红原围绕“红色草原、生态家园、牦牛之乡、旅游天堂”的旅游发展思路,着力打造大草原旅游精品景区,增强红原大草原旅游产品吸引力,打造红原大草原国家公园。 一是做好做响大草原生态观光旅游。该县围绕省道209、301线国家公园景观长廊,重点开发六个景区、建好五个旅游...
2008-05-05 编辑:admin 21785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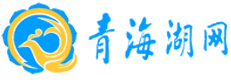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