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域藏文文书中所谓phod kar“吐火罗”考
作者:杨铭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时间:2025-12-23 09:06:07
点击数:
摘要:出自唐代及以后的藏文文献,记载吐蕃政权建立前后的千户部落中,出现了phod kar这个名称,有学者认为其来源于thod kar一词,后者就是隋唐时期“吐火罗”一词的藏文名称。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藏汉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分析后认为:虽然在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和苯教文献中,thod kar(又作thod dkar)一词被用以指中亚、西亚的国家或民族,但是在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语境中,并无“吐火罗”的明确含义。相反,该词更可能指向吐蕃本土千户部落,其地理分布与名称表明与中亚吐火罗人无直接关联。
关键词:唐代西域;藏文文书;吐火罗;thod dkar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托马斯在其著作《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中,依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提出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的吐蕃千户名称phod kar来源于thod kar一词,后者就是隋唐时期“吐火罗”一词的藏文名称。[1]笔者检索吐蕃时期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发现托马斯所做的联系并不成立。只是在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和苯教文献中,确实发现thod kar(又作thod dkar,意为扎白巾的人)一词被用以指中亚、西亚的国家或民族,该词的词源似乎来自梵文的吐火罗(Tukhra)。[2]但是在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中,thoddkar(kar)一词并没有包含吐火罗的含义。那么这里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吐蕃时期phod kar一词的具体来源与含义,二是后弘期藏传佛教和苯教文献中thod kar(thod dkar)一词的来源与流布。对于后者,作者已另文撰述。在这里仅讨论前一问题,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吐火罗”一词在藏文文献中的书写
吐火罗属于西方学者所称的印欧人,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西亚或东南欧,希腊文拼作Τόχαροι,梵文写作Tukhra。该族后来渐次东迁,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作为印欧人的一支,吐火罗人已经分布在从中亚到中国河西走廊这一大片区域,就是史书所称的位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月氏为匈奴所破,大部分迁葱岭以西。当此之时,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西迁的吐火罗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结束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建立起东扼葱岭,西接波斯,北自铁门,南到大雪山(兴都库什山),以蓝市城为都城的国家,在汉语文献中称为“大夏”,而在西方文献中被称为吐火罗。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月氏人南下进入印度,还有一部分侵入安息,到2世纪左右建立起从中亚到北印度的强大帝国“贵霜王朝”,政权及其余脉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降至隋唐还可以寻觅到吐火罗的踪迹,玄奘曾到访“睹货逻国故地”,当时尚有十余小国,大者周三千余里,小者亦数百里,中心在今阿富汗北境。[3]
就在大月氏人西迁、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 结束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建立了“贵霜王朝”,直到隋唐时期这个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跨度中,起源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与吐火罗有了交往和交流。英国学者托马斯提出在《莲花生传》(10世纪)和较晚的文献《如意宝树史》中的名词tho gar、tho kar、thod dkar,均表示西部历史上的吐火罗(Thogari)或大月氏(Tokhari)。而藏文thod kar是用来译写分布于吐蕃的东北部“吐火罗人”(Tokhari)的,phod kar则是从thod kar一词转化来的,即之前某种方言将Tokhari一词传入了吐蕃,并写作thod kar,以后又演化出phod kar一词。他认为这种演化的途径单从语音上解释,就是磨擦音th-向ph-的转变。[4]印度学者纳拉扬则认为,“吐火罗”的藏语拼法东部作phod kar、thod kar,西部作tod gar、tod dkar、tod kar,言外之意是方言之间的差距造成的读音区别。简言之,东部方言的读法是送气的ph-、th-,西部方言是不送气的t-。[5]
国内学者王欣经过研究提出,藏文文书中的phod kar很可能是指活动于从敦煌至罗布泊一带南山中的吐火罗人,大概相当于于阗文书的Ttaugara,这一点与汉文和希腊文文献中的记载可相互印证。至于吐蕃文文献中的tho gar 、tho kar和thod dkar出现要晚一些,是在吐蕃进入中亚以后出现的,它们是指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6]徐文堪教授的观点与王欣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phod kar和thod kar的区别在于,前者可能与“小月氏”有关,言下之意后者与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有关。[7]加央平措近期亦认为《贤者喜宴》《第吴宗教源流》记载的统治藏地的“马桑九族”之一的tho gar,就是指的吐火罗。[8]
但是根据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研究,相当于吐罗一词的藏文拼写thod kar(thod dkar),出现在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和苯教高僧撰写的文献中,被用以指中亚、西亚的国家或民族,而该词的词源似乎来自梵文的吐火罗(Tukhra),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历史上的吐火罗曾经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区域而对吐蕃有过重要影响, 这表现在后弘期文献追溯佛教传入吐蕃时提到了吐火罗的作用[9],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在吐蕃时期的文献中该词并无后弘期才出现的含义 , 学者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忽略了前后的区别,把该词后起之义的应用大大提前了。看来具体文献得具体分析。
二、敦煌藏文文书中的thod dkar和thod kar
在出自莫高窟的敦煌藏文文献中并没有所谓的“吐火罗”(phod kar)一词,仅有表示“白帽”的thoddkar,或变体为thod kar。在P.t.1285《古藏文苯波为小邦王禳灾故事》中,提到为人治病的男性和女性巫师(gshen)分别是:从达日白山(dags ri dkar po)来的一百名白帽(thod dkar)男巫师(pho gshen):从悉布黑山(sribs ri nag mo)上来的九百名女巫师(mo gshen)。其情节描述第一段如下:
有一天,在玉若的隆孙,觊觎王位的唐巴玉唐与唐噶拉玛结成联盟;他成为了玛郭吉玛的封臣首领。唐噶拉玛仍然没有和唐巴玉唐居住在一起;于是唐巴玉唐前往“天边的北方荒野”打猎。至于玛郭吉玛,她上去寻找珍贵的羊毛。唐巴玉唐和玛郭吉玛不猎杀野味,羚羊已经逃走了。天空开始下雪了,唐巴玉唐的身体也逐渐消沉。在隆孙,唐噶拉玛忧心忡忡,以天空为见证。她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唐巴玉唐得了病的事情。然后,从达日白山来的一百个白帽男巫师聚集在一起,他们口呼“煞若若”,然后打卦,念咒语,但并没有成功治好唐巴玉唐。而九百名女巫师则聚集在悉布黑山上,她们打卦,念咒语,但同样也没有成功地治好唐巴玉唐。一名信奉苯教的行者(?)来了,他是一个名叫宗瓦的玛域苯波。他用雪水清洗唐巴玉唐脸上的脓包,用湖里的水清洗他四肢上的水泡。清洗完后,再通过作法和念咒,他就把唐巴玉唐治好了。[10]
第二、三段以及之后的内容与上引基本相同,只不过是变换了地名、人名或治病细节而已,不赘引。法国藏学家拉露认为,一百个男巫师来自达日白山,因而称之为thod dkar,意味这些男巫师是着白衣或缠白头布的,他们被叫作“白帽”,这可能是他们的外号,[11]从中看不出来包含有吐火罗的任何元素。
而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6《小邦邦伯家臣世系》中,紧接象雄之后列于第二位的娘若切喀尔(myang rovi pyed kar)的小邦王,名为rtsang rjevi thod kar,国内学者并未对托马斯的说法做出反应,在相关藏汉对译或引用中多未标注“吐火罗”之名,而是译为“藏王兑噶尔”或“藏王拓噶尔”:[12]另有 P.T.1290《小邦邦伯家臣表》记载略同,其中正面第4行和背面第5行两处,均记载为“藏王兑噶尔”(rtsang rjevi thod kar)。[13]现已知娘若的地理位置在今日喀则白朗县境内,属于后藏地区。[14]
此外,后弘期的藏文《弟吴宗教源流》《王统日月宝串》和《贤者喜宴》亦有关于娘若小邦和小王的记载。藏文本《弟吴宗教源流》相应的段落为“娘茹恰噶尔之域(yul myang ro mchad dkar),王为藏杰兑噶尔(rgyal po rtsang rje thod kar),家臣为奔(ban)”。[15]《王统日月宝串》中的《太阳王系》记载的12个小邦名称,其中本文讨论的娘若小邦在小邦排序中位居第三,作“在后藏上部地方(gtsang stod),有藏王托嘎尔(gtsang rje thod dkar)。”[16]《贤者喜宴》记载第一章第四节“古代十二小邦”的第三个是:“娘若琼嘎(myang ro phyong dkar)之地,藏王兑噶尔(gtsang rje thong dkar),大臣为囊(gnang)”。①以上数种藏文文献记载的娘若(myang ro)的地理位置虽然名称略有差异,但均属于后藏之上部地区,也就是后藏的西部地区,[17]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吐火罗应无关系。而小邦王名中虽然均含有thod kar、thod dkar和thong dkar这种拼写方式,但同样也丝毫看不出与吐火罗有什么关系。
三、西域藏文文书中的phod kar一词辩正
截至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记载phod kar一词的文书,均出自新疆和田北面的麻札塔克古堡遗址,一共三件,两件写本,一枚简牍。其中一件写本《于阗某地吐蕃人、于阗人名册》,提到了在吐蕃统治下的于阗某地,来自吐蕃若干千户的人员与当地于阗人一起执守的名单:
在……之孜(rtse),两个吐蕃人,一个于阗人。在达孜(stag rtse)之赤古觉(khri skugs vjor),三个吐蕃人,(即)仲巴(grom pa)部落的男子则孔,娘若(myang ro)部落的洛郎墨穷,蔡莫巴(rtsal mo pag)部落的纳雪塔桑。在切玛朵之孜(bye ma vdord gyi rtse,意译为“沙石之岭”),两个吐蕃人,一个于阗人,(即)雅藏(yang rtsang)部落的普米克通,俄卓巴(vo tso pag)部落的索迪科,坚列(jam nya)乡的于阗人则多。在于阗玉姆(ho tong gyu mo),两个吐蕃人,一个于阗人,即 phod kar[部落]的……。[18]
另一枚简牍(M.Tagh. 0291)记录到:“phod kar部落的噶瓦鲁(ska ba klu)”。[19]以上两件文书的记载虽然简单,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个信息,即phod kar 是一个吐蕃部落,因为前一件文书说在于阗玉姆执守的两名吐蕃人出自“phod kar部落”。
第三件写本题名《某庄园呈达热大人书》,这件文书的正面是来自六个庄园面呈塔桑阁下的请愿书,背面第1行为一件不同的文书。但是对这件文书中的phod kar的识读和翻译,目前还有很多歧义。托马斯把文书的第二行的末尾转写成pho nya[ph]od kar,并把相关段落译为:“二十九日夜,从羌若(skyang ro)送来了三袋和十一捆东西。根据我们发出的信件,命令这个传令兵在纳(nag)平原和我们会合。他是一个phod kar人”,意即吐火罗人。[20]但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对第二行末尾的转写是pho[bro bo dkar)/drag)], 并说pho [bro] 或许可以读成pho nya“使者”或“信使”,很明显他没有认同托马斯的释读[21]第三个翻译这一段藏文的贡保扎西教授,虽然,其藏文转写与托马斯的一致,但他把pho nya[ph]od kar译成:“二十九日夜,从羌若(skyang ro)运来了三个口袋和十一捆东西。并盖有使者印记,这个使者在唐纳(thang nag)平原与我们会面。”亦无任何吐火罗的信息。[22]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此件文书中是否能够读出phod kar只好存疑。根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的记载,吐蕃时期在其本土和扩展地区共设置有五茹、六十一千户,其中位于西部的“叶茹”千户名称如下:
东钦(ston chen)、象钦(shang chen)、朗迷(lang mi)、波噶(phod dkar)、辗克尔(nyen mkhar)、章村(vgrang mtshams)、约若(sbo rab)、松岱(gzong sde)、象小千户、西侧近卫队。[23]
其中的“波噶(phod dkar)千户”,如果按照托马斯的观点,是要读作“吐火罗千户”的。虽然8至9世纪中叶在吐蕃统治的河陇以及西域地区,确曾驻扎过某些来自吐蕃本土的千户,见于鄯善、于阗两地出土古藏文写本和木简上的吐蕃千户就有28个,其中曾经进出过于阗的确实有phod kar千户。[24]但是把位于吐蕃后藏地区的“叶茹”所属千户之一,说成是来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吐火罗,这一地理关联和部落迁徙缺乏史料的说明和支撑。
注释
①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294-295.
[2] 石泰安著,耿昇译,陈庆英校订.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393.
[3]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0-101.
[4]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294-295.
[5] 纳拉扬著、徐文堪译.论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月氏人及其中国故乡[M]//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440.
[6] 王欣.吐火罗之名考[J].民族研究,1998(3):73-83.
[7] 徐文堪.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M]//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23.
[8] 加央平措.古代吐火罗与象雄、吐蕃之间的雍宗苯教文化交流[J].中国藏学(藏文版),2011:(1).
[9] 焦丽娜,杨铭.吐蕃与吐火罗的宗教文化交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1-27(005).
[10] 拉露著,韦舒婷、杨铭译.封地、毒药和医者—伯希和收集藏文写本P.T.1285考释[J].青藏高原论坛,2022(4):50-60.
[11] Lalou,M.“Fiefs,poisons et guérisseurs”,Journal Asiatique,1958,Vol. 246(2),pp.157-201.
[12]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73.[13] Macdonald Spanien,A. et Yoshiro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ques Manuscrits de l' 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Tome II,Paris,1979,pls. 600-603.
[14][17] 阿贵.新发现藏文史籍《王统日月宝串》有关吐蕃小邦史料[J].青藏高原论坛,2016,4(3):116-120.
[15] 弟吴贤者.弟吴宗教源流(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25.
[16] 古格班智达扎.太阳王系和月亮王系(藏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86.[18] Thoma,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p.173-174;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版)[M].北京华书局,2020:170-171.
[19]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294;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20:284-285.
[20]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 Documents,London,1951,pp.240-241;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版)[M]. 北京:中华书局,2020:230-231.
[21] Takeuchi,T.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The Toyo Bunko–The British Library,1998,p.51.
[22] 杨铭、贡保扎西、索南才让.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选译[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20
[23] 巴俄·祖拉陈瓦 . 贤者喜宴(藏文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87.
[24] 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修订版)[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254-267.
作者简介
杨铭,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教学与科研,尤其致力于结合敦煌西域汉藏文书以研究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教育部、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若干。出版《氐族史》《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等专著多部,合作翻译、出版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武内绍人《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敦煌研究》《西域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关键词:唐代西域;藏文文书;吐火罗;thod dkar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托马斯在其著作《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中,依据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提出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的吐蕃千户名称phod kar来源于thod kar一词,后者就是隋唐时期“吐火罗”一词的藏文名称。[1]笔者检索吐蕃时期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发现托马斯所做的联系并不成立。只是在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和苯教文献中,确实发现thod kar(又作thod dkar,意为扎白巾的人)一词被用以指中亚、西亚的国家或民族,该词的词源似乎来自梵文的吐火罗(Tukhra)。[2]但是在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中,thoddkar(kar)一词并没有包含吐火罗的含义。那么这里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吐蕃时期phod kar一词的具体来源与含义,二是后弘期藏传佛教和苯教文献中thod kar(thod dkar)一词的来源与流布。对于后者,作者已另文撰述。在这里仅讨论前一问题,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吐火罗”一词在藏文文献中的书写
吐火罗属于西方学者所称的印欧人,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西亚或东南欧,希腊文拼作Τόχαροι,梵文写作Tukhra。该族后来渐次东迁,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作为印欧人的一支,吐火罗人已经分布在从中亚到中国河西走廊这一大片区域,就是史书所称的位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月氏为匈奴所破,大部分迁葱岭以西。当此之时,希腊人统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西迁的吐火罗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结束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建立起东扼葱岭,西接波斯,北自铁门,南到大雪山(兴都库什山),以蓝市城为都城的国家,在汉语文献中称为“大夏”,而在西方文献中被称为吐火罗。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月氏人南下进入印度,还有一部分侵入安息,到2世纪左右建立起从中亚到北印度的强大帝国“贵霜王朝”,政权及其余脉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降至隋唐还可以寻觅到吐火罗的踪迹,玄奘曾到访“睹货逻国故地”,当时尚有十余小国,大者周三千余里,小者亦数百里,中心在今阿富汗北境。[3]
就在大月氏人西迁、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 结束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建立了“贵霜王朝”,直到隋唐时期这个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跨度中,起源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与吐火罗有了交往和交流。英国学者托马斯提出在《莲花生传》(10世纪)和较晚的文献《如意宝树史》中的名词tho gar、tho kar、thod dkar,均表示西部历史上的吐火罗(Thogari)或大月氏(Tokhari)。而藏文thod kar是用来译写分布于吐蕃的东北部“吐火罗人”(Tokhari)的,phod kar则是从thod kar一词转化来的,即之前某种方言将Tokhari一词传入了吐蕃,并写作thod kar,以后又演化出phod kar一词。他认为这种演化的途径单从语音上解释,就是磨擦音th-向ph-的转变。[4]印度学者纳拉扬则认为,“吐火罗”的藏语拼法东部作phod kar、thod kar,西部作tod gar、tod dkar、tod kar,言外之意是方言之间的差距造成的读音区别。简言之,东部方言的读法是送气的ph-、th-,西部方言是不送气的t-。[5]
国内学者王欣经过研究提出,藏文文书中的phod kar很可能是指活动于从敦煌至罗布泊一带南山中的吐火罗人,大概相当于于阗文书的Ttaugara,这一点与汉文和希腊文文献中的记载可相互印证。至于吐蕃文文献中的tho gar 、tho kar和thod dkar出现要晚一些,是在吐蕃进入中亚以后出现的,它们是指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6]徐文堪教授的观点与王欣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phod kar和thod kar的区别在于,前者可能与“小月氏”有关,言下之意后者与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有关。[7]加央平措近期亦认为《贤者喜宴》《第吴宗教源流》记载的统治藏地的“马桑九族”之一的tho gar,就是指的吐火罗。[8]
但是根据法国藏学家石泰安的研究,相当于吐罗一词的藏文拼写thod kar(thod dkar),出现在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和苯教高僧撰写的文献中,被用以指中亚、西亚的国家或民族,而该词的词源似乎来自梵文的吐火罗(Tukhra),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历史上的吐火罗曾经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区域而对吐蕃有过重要影响, 这表现在后弘期文献追溯佛教传入吐蕃时提到了吐火罗的作用[9],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在吐蕃时期的文献中该词并无后弘期才出现的含义 , 学者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忽略了前后的区别,把该词后起之义的应用大大提前了。看来具体文献得具体分析。
二、敦煌藏文文书中的thod dkar和thod kar
在出自莫高窟的敦煌藏文文献中并没有所谓的“吐火罗”(phod kar)一词,仅有表示“白帽”的thoddkar,或变体为thod kar。在P.t.1285《古藏文苯波为小邦王禳灾故事》中,提到为人治病的男性和女性巫师(gshen)分别是:从达日白山(dags ri dkar po)来的一百名白帽(thod dkar)男巫师(pho gshen):从悉布黑山(sribs ri nag mo)上来的九百名女巫师(mo gshen)。其情节描述第一段如下:
有一天,在玉若的隆孙,觊觎王位的唐巴玉唐与唐噶拉玛结成联盟;他成为了玛郭吉玛的封臣首领。唐噶拉玛仍然没有和唐巴玉唐居住在一起;于是唐巴玉唐前往“天边的北方荒野”打猎。至于玛郭吉玛,她上去寻找珍贵的羊毛。唐巴玉唐和玛郭吉玛不猎杀野味,羚羊已经逃走了。天空开始下雪了,唐巴玉唐的身体也逐渐消沉。在隆孙,唐噶拉玛忧心忡忡,以天空为见证。她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唐巴玉唐得了病的事情。然后,从达日白山来的一百个白帽男巫师聚集在一起,他们口呼“煞若若”,然后打卦,念咒语,但并没有成功治好唐巴玉唐。而九百名女巫师则聚集在悉布黑山上,她们打卦,念咒语,但同样也没有成功地治好唐巴玉唐。一名信奉苯教的行者(?)来了,他是一个名叫宗瓦的玛域苯波。他用雪水清洗唐巴玉唐脸上的脓包,用湖里的水清洗他四肢上的水泡。清洗完后,再通过作法和念咒,他就把唐巴玉唐治好了。[10]
第二、三段以及之后的内容与上引基本相同,只不过是变换了地名、人名或治病细节而已,不赘引。法国藏学家拉露认为,一百个男巫师来自达日白山,因而称之为thod dkar,意味这些男巫师是着白衣或缠白头布的,他们被叫作“白帽”,这可能是他们的外号,[11]从中看不出来包含有吐火罗的任何元素。
而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1286《小邦邦伯家臣世系》中,紧接象雄之后列于第二位的娘若切喀尔(myang rovi pyed kar)的小邦王,名为rtsang rjevi thod kar,国内学者并未对托马斯的说法做出反应,在相关藏汉对译或引用中多未标注“吐火罗”之名,而是译为“藏王兑噶尔”或“藏王拓噶尔”:[12]另有 P.T.1290《小邦邦伯家臣表》记载略同,其中正面第4行和背面第5行两处,均记载为“藏王兑噶尔”(rtsang rjevi thod kar)。[13]现已知娘若的地理位置在今日喀则白朗县境内,属于后藏地区。[14]
此外,后弘期的藏文《弟吴宗教源流》《王统日月宝串》和《贤者喜宴》亦有关于娘若小邦和小王的记载。藏文本《弟吴宗教源流》相应的段落为“娘茹恰噶尔之域(yul myang ro mchad dkar),王为藏杰兑噶尔(rgyal po rtsang rje thod kar),家臣为奔(ban)”。[15]《王统日月宝串》中的《太阳王系》记载的12个小邦名称,其中本文讨论的娘若小邦在小邦排序中位居第三,作“在后藏上部地方(gtsang stod),有藏王托嘎尔(gtsang rje thod dkar)。”[16]《贤者喜宴》记载第一章第四节“古代十二小邦”的第三个是:“娘若琼嘎(myang ro phyong dkar)之地,藏王兑噶尔(gtsang rje thong dkar),大臣为囊(gnang)”。①以上数种藏文文献记载的娘若(myang ro)的地理位置虽然名称略有差异,但均属于后藏之上部地区,也就是后藏的西部地区,[17]与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吐火罗应无关系。而小邦王名中虽然均含有thod kar、thod dkar和thong dkar这种拼写方式,但同样也丝毫看不出与吐火罗有什么关系。
三、西域藏文文书中的phod kar一词辩正
截至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记载phod kar一词的文书,均出自新疆和田北面的麻札塔克古堡遗址,一共三件,两件写本,一枚简牍。其中一件写本《于阗某地吐蕃人、于阗人名册》,提到了在吐蕃统治下的于阗某地,来自吐蕃若干千户的人员与当地于阗人一起执守的名单:
在……之孜(rtse),两个吐蕃人,一个于阗人。在达孜(stag rtse)之赤古觉(khri skugs vjor),三个吐蕃人,(即)仲巴(grom pa)部落的男子则孔,娘若(myang ro)部落的洛郎墨穷,蔡莫巴(rtsal mo pag)部落的纳雪塔桑。在切玛朵之孜(bye ma vdord gyi rtse,意译为“沙石之岭”),两个吐蕃人,一个于阗人,(即)雅藏(yang rtsang)部落的普米克通,俄卓巴(vo tso pag)部落的索迪科,坚列(jam nya)乡的于阗人则多。在于阗玉姆(ho tong gyu mo),两个吐蕃人,一个于阗人,即 phod kar[部落]的……。[18]
另一枚简牍(M.Tagh. 0291)记录到:“phod kar部落的噶瓦鲁(ska ba klu)”。[19]以上两件文书的记载虽然简单,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个信息,即phod kar 是一个吐蕃部落,因为前一件文书说在于阗玉姆执守的两名吐蕃人出自“phod kar部落”。
第三件写本题名《某庄园呈达热大人书》,这件文书的正面是来自六个庄园面呈塔桑阁下的请愿书,背面第1行为一件不同的文书。但是对这件文书中的phod kar的识读和翻译,目前还有很多歧义。托马斯把文书的第二行的末尾转写成pho nya[ph]od kar,并把相关段落译为:“二十九日夜,从羌若(skyang ro)送来了三袋和十一捆东西。根据我们发出的信件,命令这个传令兵在纳(nag)平原和我们会合。他是一个phod kar人”,意即吐火罗人。[20]但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对第二行末尾的转写是pho[bro bo dkar)/drag)], 并说pho [bro] 或许可以读成pho nya“使者”或“信使”,很明显他没有认同托马斯的释读[21]第三个翻译这一段藏文的贡保扎西教授,虽然,其藏文转写与托马斯的一致,但他把pho nya[ph]od kar译成:“二十九日夜,从羌若(skyang ro)运来了三个口袋和十一捆东西。并盖有使者印记,这个使者在唐纳(thang nag)平原与我们会面。”亦无任何吐火罗的信息。[22]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此件文书中是否能够读出phod kar只好存疑。根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的记载,吐蕃时期在其本土和扩展地区共设置有五茹、六十一千户,其中位于西部的“叶茹”千户名称如下:
东钦(ston chen)、象钦(shang chen)、朗迷(lang mi)、波噶(phod dkar)、辗克尔(nyen mkhar)、章村(vgrang mtshams)、约若(sbo rab)、松岱(gzong sde)、象小千户、西侧近卫队。[23]
其中的“波噶(phod dkar)千户”,如果按照托马斯的观点,是要读作“吐火罗千户”的。虽然8至9世纪中叶在吐蕃统治的河陇以及西域地区,确曾驻扎过某些来自吐蕃本土的千户,见于鄯善、于阗两地出土古藏文写本和木简上的吐蕃千户就有28个,其中曾经进出过于阗的确实有phod kar千户。[24]但是把位于吐蕃后藏地区的“叶茹”所属千户之一,说成是来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吐火罗,这一地理关联和部落迁徙缺乏史料的说明和支撑。
结语
本文通过批判性分析藏文文献术语的历史性演变,澄清了“phod kar”与“吐火罗”关联的学术误读,为吐蕃与中亚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思路在于,藏文词汇thod kar与梵文词Tukhra“吐火罗”语近,故在后弘期的佛、苯文献中被借以指中亚、西亚的国家或民族,且源流被上溯到中古时期的吐火罗,但是在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中,phod kar一词并没有吐火罗的含义,因而关于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的吐蕃部落phod kar来源于thod kar一词,意指吐火罗的观点似难成立。注释
①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参考文献
[1]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294-295.
[2] 石泰安著,耿昇译,陈庆英校订.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393.
[3]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0-101.
[4]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294-295.
[5] 纳拉扬著、徐文堪译.论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月氏人及其中国故乡[M]//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440.
[6] 王欣.吐火罗之名考[J].民族研究,1998(3):73-83.
[7] 徐文堪.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M]//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23.
[8] 加央平措.古代吐火罗与象雄、吐蕃之间的雍宗苯教文化交流[J].中国藏学(藏文版),2011:(1).
[9] 焦丽娜,杨铭.吐蕃与吐火罗的宗教文化交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1-27(005).
[10] 拉露著,韦舒婷、杨铭译.封地、毒药和医者—伯希和收集藏文写本P.T.1285考释[J].青藏高原论坛,2022(4):50-60.
[11] Lalou,M.“Fiefs,poisons et guérisseurs”,Journal Asiatique,1958,Vol. 246(2),pp.157-201.
[12]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73.[13] Macdonald Spanien,A. et Yoshiro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ques Manuscrits de l' 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Tome II,Paris,1979,pls. 600-603.
[14][17] 阿贵.新发现藏文史籍《王统日月宝串》有关吐蕃小邦史料[J].青藏高原论坛,2016,4(3):116-120.
[15] 弟吴贤者.弟吴宗教源流(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25.
[16] 古格班智达扎.太阳王系和月亮王系(藏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86.[18] Thoma,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p.173-174;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版)[M].北京华书局,2020:170-171.
[19]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Documents,London,1951,p.294;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20:284-285.
[20] Thomas,F.W.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 Documents,London,1951,pp.240-241;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版)[M]. 北京:中华书局,2020:230-231.
[21] Takeuchi,T.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The Toyo Bunko–The British Library,1998,p.51.
[22] 杨铭、贡保扎西、索南才让.英国收藏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选译[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20
[23] 巴俄·祖拉陈瓦 . 贤者喜宴(藏文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87.
[24] 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修订版)[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254-267.
作者简介
杨铭,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教学与科研,尤其致力于结合敦煌西域汉藏文书以研究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教育部、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若干。出版《氐族史》《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等专著多部,合作翻译、出版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武内绍人《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敦煌研究》《西域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文章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相关推荐
西宁唱区拍摄为灾区祈福MV潜心祈祷
岗底斯组合成员才吉卓玛 岗底斯组合成员斗合卓吉 岗底斯组合成员俄却吉 才吉拉毛 日前,全国上下都密切关注着西南旱情的进展,继青海卫视制作了《花儿的祈福》公益MV后,“2010·九阳·绿色中国·花儿朵朵”西宁唱区也积极响应,组织西宁本地...
2010-04-09 编辑:admin 17328青海湖畔武大学子举行大型环保签名活动
7月20日的青海湖比往常热闹许多,正值国际环湖自行车赛青海湖赛段的活动期间,游人如织。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这个美丽的时刻,有一个特殊的团体,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环保签名活动现场 他们就是武汉大学赴青海省实践团队,为宣传环保,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他们...
2010-07-22 编辑:admin 20435海西成为青海首批获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州
近日,青海省十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决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自2016年7月1日起可以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这标志着海西成为立法法修改后我省首批获得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自治州。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2016-06-28 编辑:admin 22912黄河源头玛多县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
2012年3月9日,一群藏羚羊在雪地上嬉戏。 2012年4月21日,一只鸬鹚掠过星星海。 2012年3月18日,扎陵湖乡一名牧民牵着一只藏獒走过雪地。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有“黄河源头第一县”之称。目前玛多县境内的藏原羚数量已达4万只以上,比10年...
2012-05-03 编辑:admin 22697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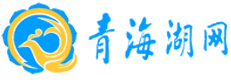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