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达吉:秃鹫(短篇小说)
作者:元旦达吉
来源:《青海湖》2025年第5期
时间:2025-05-13 08:33:29
点击数:
秃鹫
元旦达吉
元旦达吉
江巴谛视着巴央脸上的淤青,怒火燃起,怒气充斥他体内的血液,血液近乎沸腾起来。
“我若不宰了他,我就不是人。”从江巴嘴里蹦出。
江巴端详着眼前的巴央,身体秀颀,细瘦的脖颈连接一张高颧骨的瘦脸,宛然一只直立的瘦母羊。她在江巴的呵责中颤着身体,高颧骨下发紫的淤青,犹如阳光照不到山岩下的阴影。江巴越看越窝火,终于抬起拳头,锤砸桌面,桌上半碗茶水飞溅出几滴,巴央的内心也猛跳了几下。眼泪就从震颤的心里挤了出来,她抬起胳膊挽着脸,低头抽噎。像哭诉,也像喃喃地哀求。
江巴看着抽噎的巴央,攥紧的拳头,攥得抖动。看到八岁的才加像一只受惊的羔羊。江巴才缓和语气,松开拳头,起身走向屋外。走到院子里,又回头叫嚷:我一定要宰了他,那个畜生在哪?江巴刻意大声喊叫,想让屋里的巴央听见,也有意让院外的人听见。
巴央只敢躲在屋里,怀里拥着才加。她看着窗外,哭声减弱,但头连同肩部还在上下抖动。
江巴在院子外,握着摩托车把手。在几个闻声赶来的邻居面前,大声叫嚷:那个畜生,不是男人。只会欺负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我要宰了他。这句话裹挟着风灌入围观的邻居心里。江巴此时就像一个去复仇的骑士,蹬着摩托车出征。
山路上扬起一道灰尘,面包车的车轮卷袭着灰土,像一匹马在土路上发狂。陈旧的铁皮车和晃荡的车门,各自发出尖锐的金属吱吱声。尕松多杰双手扶着方向盘,头发蓬乱得如九月的杂草,眼球内布满血丝,一股戾气散发在全身。嘴里呵责:穷婆子,我一定要再揍一次。每次出门,总拿孩子压我?我每次回来带糌粑给他们,已经能养活这母子俩了,却非要哭穷……
尕松多杰一手握转方向盘,一手掰下变速杆,猛然停车。下车,仰视着远处山顶,一群秃鹫在空中盘旋。他猜测远处会是什么尸体招来了这群秃鹫。可能是落单的野狼尸体或是被猛兽袭击的牦牛残骸吧。他想,秃鹫会在天空中盘旋数天,确定尸体不再动弹后,才会落地啃食尸体,是个狡猾的禽类。总之他觉得这是不祥的兆头。他钻进面包车的瞬间,往地面啐一口痰,紧随一句话,呸!真是晦气。
面包车停靠在一间土平房外,尕松多杰走进去,土平房内响着麻将牌碰撞的杂乱声。此时天空沉下了乌云,弥漫屋顶和山脊。直到翌日的晨曦,尕松多杰佝偻着身子,走出门。
夜晚的乌云似乎涂抹了他的脸,形成一层污垢。两眼泛红,眼角凝固着泪渍,眼屎镶嵌在他的眼角,像是山羊股槽内没有脱落的羊粪蛋。仅有的300多元,也输在了小赌场内。他把输钱的霉运归咎在秃鹫绕空的征兆。他启动了车,铁皮震颤的面包车油标只剩两格。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埋怨老天爷对他不公,没有给他好运,没过好生活,麻将也没有赢过,更没有娶到想要的女人。如果扎瓦家的大女儿和他过日子,他确定生活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艰难。扎瓦家的大女儿虽是牧民,但她家底殷实,人勤快,长相又好看,面色白里透红。半圆的眉毛,圈在圆亮的眼睛上。头巾遮住嘴鼻后,那双圆圆亮亮的眼睛,像是涌动在草地间的两眼山泉,勾住了尕松多杰的心。
尕松多杰最近见扎瓦家的大女儿——吉索,是在一年前雨天的一个傍晚,暴雨在山坡上驱散了吉索家的牦牛,吉索像被牦牛捉弄的孩子,她的哭声里夹杂着呵责,脸被雨水浸湿。牦牛在纷乱的雨中混乱,污泥被杂乱的四蹄踩踏,泥水四溅,也溅在藏袍上吉索的,雨水由上而下浇灌,泥水由下而上四溅。这混乱的场面,竟被突然出现的尕松多杰扭转。他手中的投石绳像一把火铳,随着一声声“啪”,精准地打在顽固的牦牛身上,瞄哪儿,打哪儿。牦牛瞬时变得乖巧。挥动的投石绳发出击声,让嘈杂雨声都静默,雨势变弱,牦牛群聚拢,朝着尕松多杰的掌控的方向前行。这一刻吉索止住眼中的泪水,露出了一丝暧昧的微笑,这全都是尕松多杰观察到的。
牦牛赶到吉索家门口,吉索先让几头牦牛进牛圈,她站在牦牛群中间,是有意阻断和尕松多杰的距离。她只是走进家门时回头望了一下门口,像是看尕松多杰,也像是用目光收揽牦牛。但尕松多杰确定这是吉索对他留恋的好感。
可现在他对吉索仅存的幻想也破灭了,又想起家中烦心的巴央,和闹心的孩子,怨气变重。烦恼在他的心间和脑海中淤积,胸闷烦躁。不知不觉中,汽车竟然开到了吉索家的方向,远远看到吉索家房子时,车停了下来。面包车里的他,像极了在远处窥视羊圈的狼,不敢冲到院子里撕咬在羊圈里待宰的羔羊。他看着吉索家的房屋和院子,最后目光锁在了她家的门口,回想起他送吉索到她家门口。她的眼神那么勾人,仿佛再多一些时间,他就能进入吉索家一般。他远眺着吉索家的木门,感觉吉索就会从木门中出现,他还幻想着吉索从木门中走出,头上裹着那天雨中的鲜红头巾,甚是吸引心魄。尕松多杰看了不知多少时刻,野风吹刮着地上的尘埃,模糊了吉索家的房子,他泛起了困意。眼睛变得沉重,一晚没有合眼的困乏,加重了他的睡意,他摆平靠背,靠倒在车里,竟然也酣睡起来。
面包车里,袭来一丝寒意,车窗外的景色变得暗淡,吉索家的房子也隐秘在朦胧的夜色中。尕松多杰胃里一阵抽搐,他在面包车里饿醒了。面包车里弥漫着异味,是他身上汗渍和数天没有洗脚的酸味。他伸手摸出装在塑料袋里的饼子,在干渴的嘴努力匀出一点口水,艰难地咽下饼子,像蛇活吞鸡蛋。胃里的难受,让他终于放弃了对吉索望一眼的心念。发动车又怀着满腔的怨气离去。这怨气是双重的,一是未能窥见吉索的不甘,还有是要回到巴央和孩子哭闹的家里。面包车行驶在颠簸曲折的土路上。尕松多杰不自觉地加快了车的速度。困意和饥饿催着他想快速回到家中,到家至少能吃热乎的糌粑和暖身的奶茶。车子快速行驶,在夜色中穿梭,像是在牛粪堆里跃出的火星子忽闪而过。车速越快困意越重,他频繁地眨着眼睛,试图让眼睛休息片刻。就在他闭眼的霎时间,一个灰色的人影,在道路中间一晃而过。紧接着一声扰乱夜空的激荡声,震碎了夜空的宁静。车身大幅度地颠簸。尕松多杰才猛地睁开眼睛,整个人一下精神起来。方向盘在手中左右拧动,车身压过人影随惯性前驱一段路后,他才将车子刹住。他顿感不妙,从车上跳下来。随着土路上划过的车轮影子,看到数十步处,一个男人仰面倒地,张着嘴,嘴角流淌着黑色的粘液。身上衣服被车底金属刮破,像是剥皮一半的橘子皮。尕松多杰蹲下慌张地忙问:怎么了,怎么了!
地上的人影,发出极弱的呻吟声,像是人要断气时从嗓子内呼出的弱音。人影不再动弹,尕松多杰颤动着手轻轻摸索着人影的一边,不敢用力抚摸,只是不知道要提起来,还是拉一把。他最终站起身,奔向面包车的位置,调转车头,将车灯照向地上的人影。车灯照着地上的人影,才看清是村里的疯子,是个外地流浪过来的流浪汉,尕松多杰从慌张的神情变成恼怒,边下车,边呵责:你怎么跑到路中间,你这个倒霉运的家伙。全是你的错。是你蹿到路中间的。
躺着地上的流浪汉,嘴里溢出深色的血液,微微颤了一下下巴,直至不再有任何细微的动弹。与夜色中的一块岩石一般变得僵硬。
尕松多杰起身,垂下双臂,继续斥责:寿尽的穷鬼,死在车下也是一种解脱,不用再挨饿,乞讨了。只是害了我。他东张西望,看着有没有人发现,也在思考着怎么处理尸体。他嘴里的斥责变成了抱怨:我就说这几天倒霉,又碰到你,倒霉至极。难怪出门时就看到秃鹫悬空,原来就是要发生这种事。倒霉!太倒霉了!
抱怨中突然止住了抱怨,脑海中闪出一道诡计。他壮着胆子,将流浪汉的尸体扛在肩上,他心里想着这发臭的家伙,没有洗过澡,发霉的味道似乎是从他裸露的肌肤内散发出来。从流浪汉嘴里淌出的血液腥味,要比他身上散发的气味容易接受得多。他用嘴呼吸,尽量不让空气和味道从鼻子中吸入。他将流浪汉的尸体扔在面包车后面,消失在夜色之中。
20年后,傍晚。
通向乡村的土路,已经铺上了柏油沥青。土墙的房子,也融合了水泥和空心砖的结构。尕松多杰的家里,除了孩子个子变高,巴央干瘦的脸变得焦黄,皱纹变得密集,肌肤俨然成了暴晒干瘪羊肚一般以外。他家依旧没有改变。泛黄的土墙房子,随着野风脱落了一层泥渣。房子内只有一盏微弱的,暗沉的,落满灰尘的灯泡,散发着柔弱的黄光。显然照不亮阴沉的屋内,房子内充斥着一种幽暗的感觉。
尕松多杰已经有了圆滚的肚子,脊背也有了弯曲的弧度,乱糟的白发下,一张褶皱脸上,添了几处褐斑。但对巴央的呵责,并没有随着年纪增加而减弱。他躺在陈旧的,连翻身都嘎吱作响的木床上,让孩子不要吵闹。让巴央沏上热茶,拌好糌粑,就等着伺候他睡了一天后的饥饿和随时发怒的脾气。他起身吃着碗里的糌粑团,用茶水下咽,始终没有看向巴央和孩子。孩子垂着头,不时会从前额的头发丝间,窥觑尕松多杰咀嚼糌粑的脸,像是一只幼狼,窥探着凶残的野狼啃食动物的残躯和尸骸。孩子的眼里隐藏着怒气。巴央仍是呆滞的眼神,只是望着炉子的火,火势减弱,她就会续上牛粪。只有尕松多杰要求续茶时,她才会起身给他续茶,又坐回黝黯的角落。像是在躲避尕松多杰的目光和他的声音。
尕松多杰吃罢糌粑,又倒平躺在木床上,眼睛望着被牛粪烟熏黑的黢黑房顶,脑袋里思忖着什么。突然他猛地起身,披上上衣,走出家门,离开让他觉得压抑,黯淡的房屋。巴央和孩子竟没有一句挽留的言语,和一个目送的眼光。任由他随来随去,母子俩早已殆尽了能挽留这个随时挥拳的丈夫和这个无视孩子的父亲的勇气和能力。
20年前的夜里。
夜里,面包车在夜色中,游移。试图寻找一处藏匿尸体之地。尕松多杰在车里回望着一团黑色的尸体。车内,尸体随汽车的晃动而摇晃。尕松多杰想到,尸体一定会淌下血液,他停车将尸体上的衣服脱下,套上自己的上衣。将尸体上的衣服垫在底下,以此阻隔血液淤积车内。汽车开到一处山坳的土丘上。他下车,找到坑地,将尸体投到里边,想要埋葬尸体。他想,夜色越漆黑越能给他机会掩埋尸体。可将尸体扔在坑内后,想起自己并没有铁锹来挖地和掩埋尸体。他再次将尸体扔回面包车里,借助夜色寻觅藏尸之地。他最终在深山里停车,回头看着尸体,又探视车外的夜色中的景物。远处山的轮廓,近处车灯照亮的范围,让他觉得没人发现他的行踪,是藏尸的绝佳机会。但他也没有找到藏尸的地方。他想过将尸体扔进河里,但尸体总会漂上水面。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思索着开始责骂乞丐,要死,不早饿死、病死,偏偏死在我的车底下。我真是倒霉……难怪前天出门碰到秃鹫悬空,真是不祥之兆,麻将才会输,运气才会变差。责骂中他脑袋中若有诡计乍现。
他将自己的裤子脱下,套在尸体上。忍着将乞丐发霉发臭的裤子穿到自己的身上。脑袋里想到了一系列的处理尸体的“妙招”。
翌日下午,尕松多杰坐在麻将馆里,比以往变得健谈。打着麻将嘴里不时地说着他听说的谣言。
“听说了吗?村里的一个小孩被山神带走藏在山里。三天后他的家人才找到的。据那个小孩说被山神带到山里藏匿了三天,喂的是兔奶。”尕松多杰缓慢地摸着麻将,睁大眼睛说。
其中一个人说,是呀!有这种,我们村里也有一个妇女被山神召唤而消失。到现在还没找到。
小麻将室里,开始闲聊山神和夜路碰见诡异的事。
过了几日,村里传出了乞丐失踪的消息,有传言说流浪到了其他地方,还有人说是被山神召进山里。我当时参警已有五年,我并不相信那些传言,所谓村上被山神招走的妇女,只是他和情妇逃跑,她的家人羞愧,才造谣是山神召唤罢了。得知村上的乞丐不见数日后,我带着一名年轻的协警员,去寻找乞丐的下落。
走访村民得知,流浪汉是从另一个村里要饭来到我们然秀村的,已有十几年了村民总会给他食物,让他活下去。其中一个村民说,他长期睡在我家院子后面,我将家里的旧藏袍和闲置的棉被铺在墙角边,让他安顿。有时家里会匀出一碗面条送他,他会吃几口,猛然起身,一脚踢飞碗,然后顺街道去游荡。
我带着协警员只能去流浪汉过来的村里,路途中和协警员聊着天,也不无聊。但协警员和我说起流浪汉可能被山神召走的传言。我问他,你信吗?
他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他没上过学,他的叔叔看着他在村子里无所事事,怕他惹事。于是找到他的亲戚所长,让他在村上派出所当个协警员。我知道他一定有一些对鬼神的敬畏。
他也反问我,你信吗?我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捏着衣服的前襟说:“我不信,我只信我和我手里的枪”。我顺势拍了拍别在腰间的枪。
他先是愣了一会儿,脸上就挤出一丝僵硬的笑。
到流浪汉的村里,轻易地问到了他的身世。流浪汉从小就不正常,父母双亡,靠村里人的布施生活。成年后就到处流浪。
我知道流浪汉只在村民见到他时,才会看他几眼,施舍他些衣食。其余时间,没人关心他的去向。现在他失踪了。村民也只是口头上提起他,但并没有去寻找。
回到村里,流浪汉被山神召走的消息,传遍了全村。几个年轻的村民去山头寻找流浪汉,虽然没有找到。但他们在山沟里寻找到了发霉的衣服。村民们将衣服拿到了派出所。我端详这衣服,继续猜测着流浪汉可能遭遇的情况。被野狗、野狼所害?总之不会联系到被山神召走。
我需要找到证据,才能打破流浪汉被山神勾走的谣传。我有几种猜测。
可能流浪到其他村里。
可能饿死在荒野。
可能迷路山野。
……
沿着山路寻找,我并没有抱希望,但是流浪汉的衣服,让我萌生一种不好的猜测,我寻迹捡到流浪汉衣服的地方,周遭没有一丝脚印。我想到这是第二现场,我心里只有一种遇害的猜测。但活不见人,又无从查找他的下落。
村里流浪汉被山神勾走的谣传,愈发发酵。我也担心,流浪汉找不到的时间愈长,被山神勾走的消息愈会被实锤,之后流浪汉的失踪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流浪汉遗落的上衣,是我想继续寻找他的信念。
时间总会悄无声息地消失,时间也在村子的各处流逝。对于我们的村落来说,时间在山坳上流逝,后来,山上的牦牛数量多了些。时间在河里流淌,现在,河边的人家多了几户。时间也在村子的荒地上掠过,此时,多了几串外乡人的脚印。时间已过20多年,我也脱去了我的警服,退休后的我,像是卸下盔甲的战士,妻子敬畏我,邻居敬重我。但是我内心还是不免感到失落。听到村上有案件发生,我总会刻意打探。只是在内心分析案情,内心也会感到满足。眼下,我的儿子已是初三的学生,儿子学习的科目比我那时上学的科目要多,还会给我讲述一些地球和人类的故事。儿子不太相信鬼神,我觉得他适合当警察,毕竟警察要与尸体打交道,处理一些冰冷的尸体时,需要把灵魂的事情暂搁脑后。
我即使退休,衰老了,但还是有人重视和照顾我的,我是幸运的。我追忆着,回溯着我的前半辈子。毕竟年老以后,只能靠往年用心付出的人和事,反刍记忆度日。我脑海中不免又闪过在村里消失匿迹的流浪汉。村里的老年人随着时光流逝,也渐渐遗忘了他。那年我若不是公安身份,我定会随年迈褪色的记忆模糊了流浪汉的身影。
这天,我的孩子睡在学校,老伴去她亲戚家帮忙张罗丧事。独自在家的我,拖着伛偻的身子去村头的小饭馆,解决晚饭。填充一下我空荡的胃和肚子里隐隐作祟的酒虫。我走进一对四川夫妇经营的小饭馆,小饭馆菜品不多,却是我们村子招待客人和改善伙食的选择。我坐在小饭馆的角落里。点了土豆丝和青椒炒肉,还要了一瓶五星啤酒。这是一个退休干部能消费的高规格菜品。我打开啤酒,猛地灌了几口,解馋了肚中的酒虫。在等待饭菜中,被隔壁吵闹的一桌人所干扰。顺着吵闹的声音望去,是年迈的尕松多杰和几个中年人,喝着啤酒,脸颊红晕,老年斑已蔓延到了他的印堂,但他年轻时的戾气仍然掩藏在他佝偻的身体内。他大声地喧哗,看样子没有改掉好嗜和嗜酒的恶习。早听说他让儿子打工,挣回的钱,供他挥霍。眼下他又开始喝酒,挥霍不多的收入。和他的那些不正经的牌友,或酒友在小饭馆里寻欢作乐。
他们并不在乎周边人的目光,昏暗的小饭馆里,食客只有我们两桌,其他客人兴许已被他们吵走,没人顾及坐在角落里的我。
两盘菜终于上桌,在我独享炒菜和啤酒时,尕松多杰那一桌的吵闹声骤增,一定为烂事而起争执,我本无心听取,但他的一句炫耀和压制对方的酒后撒泼的话,让我震惊直至无心在享受饭菜和啤酒。
他面红耳赤大嚷:穷鬼,你给我好好待着。
对面的酒鬼也不示弱,叱骂:我倒想看看你这老赌鬼有什么能耐!
尕松多杰因酒精的刺激,已经口无遮拦,怒气大增,以一种碾压的口吻怒斥:穷鬼,我让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连个渣滓都不剩。
他们一桌的几个人,早不把他的这种耍酒疯的话语当真。但我倒是想知道,他怎么能让一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冲着吵闹和顶嘴的酒鬼怒喝:我可以杀了你这个穷鬼,自然有让你消失的办法,你最好给我悄悄的。这口吻像是最后的警告。
他们仍是吵闹,仍在混乱中互相谩骂,被小饭馆的夫妇劝退,他们不欢而散。
但尕松多杰耍酒疯的话语,我仍心有余悸。到家后,耿耿于怀,在床上思忖他酒后的狂言。经过彻夜的思索和挣扎。
次日,我毅然决然地走向派出所,找到所长,对他说明我的想法。
当天傍晚,派出所的干警果然把尕松多杰带到派出所,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尕松多杰果真交代了他杀过人,毁灭尸体的事实。
听到这消息后,我回想起了20多年前失踪的流浪汉遗落的上衣上,黏附着的几根秃鹫的毳毛。
作者简介:
元旦达吉 藏族,青海省玉树人,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自然文学协会会员,玉树州作协副秘书长,玉树市作协副主席。《唐蕃古道》文学刊物副主编。2020年出版小说散文集《獒的末路》。2021年2023年入驻《中国作家网》。创作的小说、散文、杂文刊登于《中国民族报·民族文萃》《中国作家网》《当代小小说百家》《黄河文学》《精短小说》《湖南散文》《河南文学》《青海湖》《青海藏文报》等,偶写剧本,词等。
相关推荐
电影《情暖玉树》18日正式开机
一部以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为背景,讲述一位北京女志愿者救助身患白血病、但心怀舞蹈梦想的藏族小姑娘的故事,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的影片———《情暖玉树》2月18日在西宁正式开机。省政协主席白玛及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西宁市委市政府...
2011-02-20 编辑:admin 10732黄南州根顿群培社会发展协会开展助学献爱心活动
近日,黄南州根顿群培社会发展协会开展了“资助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活动,活动资助对象是黄南州四县和藏区品学兼优贫困大学生和高中生,大学生每人3000元,共20名,高中生每人600元,共65名,资助两年,共计23万元人民币。 这次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映,受助学生深为感动,纷纷表示...
2008-03-04 编辑:admin 14530海南职校入学教育综述
根据海南州教育工委、州教育局的安排,结合该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实际,开学伊始从3月3日到3月13日开展了为期10天的安全纪律师生行为养成教育中依据我校单亲、贫困、学困和需要心理辅导的学生共467人,占学生总数59%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下活动: 一是以召开主...
2015-03-17 编辑:admin 14074自行车业余挑战赛为青海环湖赛蓄力
为了满足广大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的骑行梦想,同时给即将到来的第十届青海环湖赛预热,首次更名为“挑战赛”的国际公路自行车业余热身赛6月30日在青海海北州西海镇打响。 赛会总裁判长金丽娜告诉新华社记者,该项赛事已经举办了三个年头,随着环青海湖赛品牌影...
2011-07-02 编辑:admin 12913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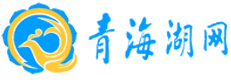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