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荣耀时刻
作者:德典白姆
来源:《西藏文学》2025年第3期
时间:2025-12-30 08:49:50
点击数:
“听说她跳河前在桥洞底下哭了一天一夜,最后就只把手机放在了岸边。”矮个子加央在众人间说着听闻。
“你瞎说什么?哭了一天一夜又是谁传出来的。人家家人都说了,找到手机才确认是跳了河。不然人都丢了,又怎么知道在桥洞底下哭了一天一夜?”白玛老头即刻反驳道。
“活该,这种女人就不该活着,不守妇道,丢我们村的脸。”卓玛在一旁吸了口鼻烟说道。
日喜村成列家的女儿在拉萨跳了河,听说是因为生活不检点,染了脏病,所以她羞愧不已,投河自尽了。次珍在集中搬迁安置点门口的凉亭内晒着太阳,听村民们讲这件大事。传消息是男人们的事,卓玛在村里以泼辣闻名,也就她可以在这些男人间插个嘴。
投了河是淹死的还是如何呢?次珍将孙子脱掉的衣服盖在膝盖上,自从搬迁到县城,她膝盖疼的毛病又加重了。县里没有村里那么暖和,搬迁之后他们的房子又被安排在五楼,每天爬楼梯走上几次,她感觉这比在村里走土路、种地还困难。跳河时可能会撞到河边的石头摔死吧?次珍想到这里,那种自小就有、双手忽地一凉的感觉又来了,她没有再想下去。
“上次那个尼姑,跳河的那个尼姑,好像就没有跳到河里去吧?”白玛一边问着一边将目光转向次珍。前几个月的那件大事,次珍是日喜村唯一的目击者,那可是全县的大事。起初日喜村的村民在跟搬迁点其他村的人说这件事时,总会提一句:“我们村洛松家的次珍看见了。”
“可不是吗?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能跳进河里才怪呢!她直接摔在了河边的石滩上,救她的人赶到的时候她还没死透,一直抽搐呢。”不待次珍开口,卓玛又用她尖锐的喉咙说出了次珍当时跟她说的那些话。此时凉亭已经围了不少人,有同村的、有同乡的、也有别乡的,在场的人听卓玛说话时,都将目光投向她,有些敬佩、有些质疑,不过多数是听声音时,习惯性地将眼睛看向声音的来源罢了。然而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卓玛的声音越来越亮,就好似这以红色装饰屋檐、周体通白的楼群是信众一般,而她正是那讲经的喇嘛,神圣无比。次珍看着卓玛的样子,心中并无多少不满,更多的是羡慕。但此时次珍的脑海正被那天飞在空中的红布所占据。
如果不去买那捆白菜,她们定然不会遇见。次珍回想那天早上的情景——她如往常一般,喂孙子吃了饭后就背上孙子的书包,牵着他的手走出搬迁安置点的大门,走向学校。送完孙子准备转向转经路时,她突然记起家里需要买些白菜,于是转身向菜市场走去。“搬迁到县里之后,连白菜都要自己去买。”次珍想起邻居四郎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为什么人家就能说清楚呢?次珍也有过类似的感想,四郎那句话早已在安置点的老人间传开,这句话多简短、真实。她怎么就说不出这种大家都十分认可的话呢?当然这句话并不被年轻一辈认同,村里气候宜人,庄稼果蔬长得也好。但是从县城到村里有三个小时车程,其中两个小时还是翻山的土路,所以年轻人都说县里更方便,打工也好找工作。次珍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她男人去世之后,家里主要是儿子和女儿做主。虽然村里的房子一直都在,但孩子们要住在县里,她便长期跟着一起,负责带孙子。她也会想念村里的生活,女儿说村子海拔比县里低,次珍肯定不知道海拔是什么,女儿也没有解释,但她知道县里更冷、更干,即使她不掌握所谓“海拔”的含义,也能感觉出来。
那天,次珍抄了近道,沿着河边走向菜市场,那条路从县城的大桥下面通过。桥很高,离河面有三十米左右。次珍正考虑除了菜还要买些什么,余光却瞥见空中有一抹红色在飞,确切地说是在桥面与河面之间的空中,有一块红布缓缓飘下,轻轻落在了河对岸的石滩上。后来她尝试着把这件事跟身边人说清楚,但大家都说一个人从高处往下跳怎么可能是那样的,肯定是快速掉下,然后狠狠地砸在石滩上。她无法说服别人,自十七岁时的那件事之后,她便再也没能让任何人从真正意义上相信自己。她也清楚,那个穿着红色僧袍的年轻尼姑掉在河对面之后,身子一阵阵颤动,鲜血从她身下流出,浸入石头的缝隙中。
岸边有人叫了救护车,救护人员到的时候,那块红布还在轻轻飘动。
“好像是因为出嫁后家庭生活不和谐就出家了,她出家后成天郁郁寡欢,最后竟然跑到县里的桥上跳了下去。”隔壁村的巴桑知道一些内幕,于是他成为了继卓玛之后楼群中的另一位“喇嘛”。次珍脑海中还是那块红布,挥之不去,于是她忍着膝盖的疼痛从板凳上站起来,招呼孙子回家。太阳还没有下山,人们依旧在那里坐着,谈论那个跳拉萨河的小媳妇。无人在意次珍的去留,除了卓玛看了她一眼以示告别,倒是小孙子的玩伴们对他依依不舍。
出家,次珍也曾差点出了家。次珍是在十七岁那年嫁到日喜村的,她的老家在县城以南六、七十公里处。出嫁那天,父亲带着她翻了一座山,山路时好时坏,他们时而骑马,时而牵马。到了镇上留宿一宿,次日又赶了一天的路穿了县城,他们才到达了日喜村所属的萨溢乡。夫家的父亲和弟弟在路口迎上他们父女二人,又在乡政府所在的村留宿一宿。第三天四个人又翻了一座山,山路时有时无,他们时而沿路,时而辟路,终于在第三天的傍晚到达了日喜村。十七岁的次珍因为能在第三天就到达出嫁的地方而倍感幸运,因为前两年她的伙伴嫁到了外地,听村里人说那个女孩在路上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她骑了马,坐了车,还渡了河。她十分感激家乡的那位女活佛,如果不是她说次珍要远嫁但不能离开本县,谁知道她要骑多久的马,走多长的路,翻多少的山。
真是曲折离奇的经历啊,次珍想起出嫁之前的事情就很疑惑,为何自己一生的精彩经历都在十七岁之前呢?回到家,次珍开始着手准备晚饭,她想煮一锅挂面,一个月前驻村工作队发的挂面还剩三袋。她弯腰把地上的高压锅拿起放在了灶台上。上了楼之后她膝盖的阵痛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缓解。
说到次珍差点出家这件事,其实还应当讲一讲更久远的事情。次珍的老家在牧区,那里有闻名西藏的冰川,当然“闻名西藏”这件事是她近几年通过抖音才知道的。年少时父亲总跟她说离夏季牧场一天半马程处的地方有雪山和冰川,传说那个地方人迹罕至,有各种神灵鬼怪出没。她还记得在她七岁那年一个冬日的晚上,屋外下着大雪,坐在炉子旁的母亲将她揽入怀中。那时炉子里火烧的噼啪声、窗外的风声和雪落的沙沙声、羊群的咩咩声还有弟弟熟睡的鼻息一齐在房中穿梭。母亲搂紧了次珍,见她迟迟不愿睡下,就讲起了关于冰川的故事。
十几年前的冬天,村里的一个人去冰川所在处寻找走丢的牦牛,到山脚时他因有些害怕眼前白色的世界而不敢向前。正当他准备往回走时,却看到半山腰处有一个移动的黑点,眯眼看去,那物体的前部还有彩色的东西,他想那可能是自家牦牛的彩色项圈,心生狂喜,勇气也随之而来,于是一个人往半山腰处走去。眼前虽是雪原,但太阳仍与雪山并肩。他并不觉得寒冷,甚至因为穿着祖辈留下的羊皮袄爬了许久的山,他越走越热,而那黑点却也同样在移动。幸运的是那黑点走得很慢很慢,离得更近时他发现那确实是一头牦牛,但比他走丢的那头大了许多。他的牦牛在村里十分有名,它壮硕、魁梧。村里老人总说他的牦牛是天庭的护卫下凡,不然怎会如此壮硕。如今竟看到一头更大的,一时间他也愣在了原地,惊诧不已。
只见那牦牛忽地转向他,两角的曲线堪称完美,毛发柔顺如抹了酥油一般。他正想着要不要将这牦牛赶回家,毕竟大概率这也是一头走丢的牦牛。不成想那牦牛突然像疯了一样冲向他,它顺坡而奔,犹如一块巨石从山上滚下,激起雪尘一片。不等他反应过来,双腿早已向山下奔去,可他不慎掉入了一个冰窟中。
所幸冰窟不深,他掉进去之后没有大碍,但是有一只脚崴了。他坐在地上,从冰窟的洞口看向天空,发觉很难凭一己之力到达地面,于是他开始环顾周围的情况,身后是一个大冰块与山连为一体,身前却是一片黑暗。从冰窟的洞口照入的光线只能照亮五米范围内的空间,而他前方的黑暗与他之间还有一块大石头。
正当他考虑是否要往黑暗中走去时,却听见一声极重的喘息声从黑暗中传来,还有一股暖风扑面。他不禁叫出声,一下跌坐在地上——不曾想那黑暗中竟亮起两个黄色的大灯笼,一闪一闪,从黑暗深处逐渐接近他。而那个人只能紧紧靠着身后的冰面,无处逃遁。只见在黑暗与光明交界处,一对巨大的鼻孔闯入阳光中,而后是长长的胡须与鼻梁。他料定这不是什么野兽,那鼻孔大到可以装下两个成年人。因为受惊过度,他在原地怔住了。
终于,那两个一闪一闪的大灯笼离他越来越近,喘息声近在咫尺,热气一阵强过一阵。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女儿,那个龙年出生的女儿如今才十二岁,如果自己丧身于此,他祈祷自己的魂魄可以乘天上的神龙回到女儿的身边。正当那灯笼即将闯入光明时,他听天由命,闭上了双眼。
喘息声在,热气也在,还有一个新的声音——水声,确切地说是放大了许多倍的舔舐声。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仅是十几秒,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是龙,是寺庙壁画上、柱子上经常出现的龙。只见那龙的双角可触至洞口处,而灯笼是龙的一双黄色的眼睛,鼻孔下的龙嘴处有一条鲜红的、宽大的舌头。那龙在舔石头,双眼紧盯着他。他只能张大嘴巴一动不动……随后那龙终于舔完,慢慢将身子缩回,隐入了黑暗中。
他感到十分惊奇,却不敢向前太多,于是他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石头前,学着龙舔了一口石头。就在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到那块石头是温热的,当舌尖碰上石头的一瞬,一股热流传遍周身,他的寒冷与饥饿也随之消散。于是自那天始,每当他感觉饿了,就都会舔一下石头,其余时间就坐在石头旁边。虽然身处冰川之内,洞口也会经常飘进雪花,但他从未觉寒意。那条龙每日都探出头舔几口石头,除此之外,就是隐在黑暗中,好似在睡觉,而他也逐渐习惯了那种鼻息。
但是他始终不知道何时才能脱身,或者在这洞中直到老死。他只能通过洞中日照时间逐渐变长、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逐渐变密来感受时光的流逝。近几天他发现那条龙每次舔完石头都会朝上看看洞外的天,这是他掉下去这么久之后,周围唯一一个变化。他下巴的胡须已经长到喉结的长度了,他渴望变化。终于在一个夜晚,那条龙又探头到了石头处,是那天的第二次。它没有舔石头而是望向了星空,他预感到可能有事即将发生。
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到了第四天,洞中迎来当天的第一缕阳光之时,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自黑暗深处传来,他马上捂紧耳朵朝黑暗看去——只见那龙如往日般将头探至石头旁张开了大嘴。只不过此次不是舔舐,而是用舌头将那大石头卷入了口中。随后龙头向上朝着洞口伸去,一条金色的身体从他旁边爬过随后伸出洞口,那片片龙鳞闪闪发光,照亮了整个洞穴,他这才发现那洞中四周皆是冰川。而最后龙尾从他身旁经过时,他一把抓住了龙尾,于是整个人立马腾空而起。出了洞口后,他立刻放手,随之顺利地掉到了地面上。抬头望去,只见那条金色的大龙曲着身子,随阵阵雷声直飞入天空的云层中。而当他终于看向周围时,却发现冬日早已过去,春天来了。
故事讲完,次珍也安心睡去,但是那天晚上她梦到了一条青色的龙从雪山顶的空中飞过。梦中她好像是看着青龙的旁观者,又像她自己就是那条龙。飞呀,飞呀,飞过了雪山、湖泊,最后来到了一片森林众多的沟地。她感觉得到青龙留恋雪山,却好似有一股看不见的神力将青龙召唤了过去。
听了故事又做了梦的次珍更想见识一下那个神奇的冰川。次珍也同故事中的女儿一样属龙,所以年幼的她固执地认为那个冰川有龙。当时父母双全,深受宠爱的她毫无畏惧,作为伙伴中的领导者,她一遍遍讲着冰川的故事,让她的伙伴们一度深信,大人口中的那片冰川深处定然盘踞着许多龙。有白色的、黑色的、青色的,最大的那条是金色的,比黄金还灿烂的金色。事实上他们没有见过多少黄金,有的仅是长辈口口声声称之为“黄金”的氧化金属饰品,它们发暗、毫无光泽。但是那时的他们,包括次珍在内,或者说以次珍为代表的他们,有的是精力和想象力,他们可以想象比黄金还灿烂的金色究竟有多耀眼。
但是这种能力在他们真正走进冰川后依次逐渐减弱,并在次珍十七岁那年荡然无存。十七岁那年次珍终于如愿见到了冰川。那年父亲带着日渐能干的女儿来到夏季牧场,而后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早晨带着女儿和同伴一道骑上马向冰川进发,他们要在傍晚时分借宿在那附近的一个村落,这样才能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抵达冰川所在处。于是第二天次珍早早地起床打好了茶,她在洗漱干净之后从怀中掏出了那个有点发黑的金手镯,那是三年前奶奶临终时留给她的嫁妆。她清楚,只有在出嫁时才能戴上手镯,她也明白,今年她就可以戴上手镯嫁入向巴家,嫁给他们家的二儿子次成。
次珍喜欢那个小伙子。
此刻,东方才有些许光亮,她还是决然将手镯戴在了左手手腕处。她觉得进入冰川就好似圆了自己十几年的梦一样,这是个神圣无比的时刻,所以她要戴上最珍贵的东西表达尊重。十年后,她牵着儿子、背着女儿走进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殿时也产生了这种感觉。在翻了一个土坡后,一众人停在山顶远眺,那几座雪山与她小时候梦到青龙的雪山一模一样,她并不觉得惊讶,因为这些年她一直坚信会如此。下了小坡来到雪山旁,父亲与众人在一处平地开始煨桑祈福。她兴奋不已,四处走动,却见一个洞口散着蓝色的光,洞口较窄仅容一人通过。
她不该进去的。
但是来到冰川的次珍又怎么可能是平日里稳重成熟的次珍,她直接走了进去。那是一个左右和顶部都是冰的冰洞,洞内并不像洞口一般狭窄。即使次珍张开双臂,也不能同时碰到两边,而举起手臂、伸伸手指却能碰到洞顶。
洞内无比安静,没有一丝声音,只有蓝色的、寒冷的光。但次珍并不觉冷,冰洞内的温度与外面没有大的差别。次珍不敢用力呼吸,只得站在原地。这就是冰川内部,可能有龙的地方。她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她也有点害怕,不知道前方究竟有什么。
后来次珍回想时,发现那是她此生最后一次自我抉择。
她稳了稳心神,用右手摸了摸手镯,准备原路返回。正在此时,她听见有个声音在叫她,仿佛很远但又十分清晰。她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传来,于是就没有理会,朝着洞口走去。
又是一声,她听得清楚,所以确定那绝对不是幻听,她的双手忽地一凉,脚下加快了速度。第三声从洞内深处传来,她猛地回头——一声惊雷从四周扑向她,随后眼前一黑,毫无知觉。
当她再次醒来时已是三天之后,她发现自己躺在了夏季牧场自家的帐篷中,里面没有其他人。
正当她疑惑之时,父亲请的喇嘛走进了帐篷中,跟在身后的父亲看见女儿醒来,喜出望外,并言真是喇嘛福泽宽厚,一来女儿就醒了。喇嘛问了问次珍整件事情的过程,又闻言次珍以前总梦到青龙在雪山上头,便脸色一沉断言道:“呼唤声、雷声、青龙都是她中了妖魔邪祟的幻术产生的幻觉。冰川本就不是什么吉祥之地,如今又被妖魔伤了身,只能出家当尼姑,了却尘事祈求佛祖庇护。”
听父亲说,当他们准备离开时发现次珍不见踪影,于是大家在四周分头找,终于在一个洞口发现了昏迷的次珍。众人见她一直不醒,又不停在她身上熏香,却也不见效果。最后只能先将她驮回牧场,再就近请个喇嘛看看。幸好第三天的清晨,她自己醒了过来。
直到现在次珍都能记起那个上午:帐篷中挤满了人,她半靠在床上,喇嘛盘腿坐在边上,人们一会儿看喇嘛,一会儿看次珍。刚从昏迷中醒来的她产生了一种在人们心中喇嘛和自己一样重要的感觉。那一刻,次珍感到无比的荣耀。
这就是次珍差点出家的原因。
吃完晚饭后,孙子拿着她的手机看抖音,而她拿着佛珠进入了那间狭小的佛堂。最近她越来越不想跟人说话,对一直在身边的孙子,她向来无话可说,而对偶尔回家的子女她也从没有什么表达欲。相反,她总喜欢回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这几年村里和县里发生了不少事,她要么亲眼看见,要么听人传说。这些只是众多奇闻中的一两个,她本不该过于上心,然而这两件事会在她念经、做饭、打扫卫生和睡觉的时候交替着闯入她的脑海中。总想起成列的女儿倒是可以理解,她丈夫家与成列家是远亲,又因在同一个村子里,所以比近亲还亲近几分。那个女孩是次珍嫁到日喜村的第七年出生的,比她的大女儿大一岁。次珍记得那个女孩也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每天穿着脏衣服跑来跑去,活泼开朗。后来去县里上中学,次珍的大女儿也是。没等那女孩初中毕业,成列一家就搬去了拉萨,女孩也没再上学。当时村里的许多人都十分羡慕成列一家,因为那里离释迦牟尼佛近。
去过拉萨的人都说,在那里生活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就近买,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当时次珍在村里唯一的商铺买一袋米都比县里贵上个五十多块。商家说:“我雇人雇车,走了这么久的山路把东西拉进来,这不得花钱吗?”当时次珍和村里人都不会想到再过个两三年,他们也可以过上那种不用翻山就能买到很多东西的生活。
为什么尼姑也总要进入脑中呢?她不是没见过死人,她的丈夫在成列一家搬到拉萨的第二年病死了。幸好不是什么传染病,不然村里人都不会将他的遗体葬入江中。日喜村离怒江近,盛行水葬,这与次珍老家盛行天葬的习俗有所差别。那天早上,人们用哈达将她的丈夫裹紧,而后放在一个木制担架上运出他们家。按风俗,次珍不能同去,黎明的黑暗中,她目送自己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最后一程,那年她刚好四十岁。
为什么尼姑总进入她的脑海?可能是因为她曾经差点成了尼姑,她想。那她又为什么没有成为尼姑呢?还是得感谢那位女活佛。那年从夏季牧场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着手准备次珍出家的事,他打听到隔壁村的深山处有一座尼姑庵,还有一位十分尊贵的女活佛,于是父亲带着次珍出发了。他们骑马来到尼姑庵所在的山脚处,父女二人又爬了半天的山才到达目的地。途中次珍说:“如果真的在这里出家,往后上山下山得受多少苦啊。”父亲走在前面低头不语。见了女活佛说明缘由,父亲叩拜请求女活佛收下次珍。女活佛年近六十,面目慈祥,看了次珍许久,方才说道:“这女子并非受妖魔所惑,入冰川时好似戴了什么物件,又因本就属龙,那冰川中的神灵误将她认作了出嫁之人了。如今出家解不了这劫数,最好嫁到一个水汽较足的地方,得离开这一带,但也不要嫁太远,需要嫁一个属龙的男子,以解此劫。”次珍没有将手镯的事讲给活佛听,如今竟然如此灵验,父亲也只得谢过活佛,回家着手准备次珍出嫁的事了。
回村后,她企图将这次神奇的经历讲给那些伙伴们听,让他们重新信服冰川有龙这一事实,巩固她作为伙伴们领导者的身份。然而伙伴们都不再相信次珍了,他们说喇嘛都说了次珍是中了妖魔的幻术产生了幻觉,所见所梦都是虚假的。后来回想时,次珍意识到好像就是从那时候起,自己失去了让别人信服的能力,那种能力同伙伴们的想象力一道荡然无存。
父亲说好了媒,要她嫁给萨溢乡日喜村一个和她同岁属龙的小伙子。这一家是次珍的舅舅帮着联系的,原先与向巴家的婚约自然取消了。次珍的父亲登门道歉,向巴家十分善解人意。又过了一个月,父亲算好了吉日带着次珍出发了。他们出发的前一晚下了一夜的小雨,次珍如儿时一般依偎在母亲怀中,哭着哭着就睡去了。而父亲听了一夜的雨,叹了一夜的气。幸运的是雨在第二天他们出门前停了,父亲的脸上终于现出笑容。在路途中的最后一座山顶,看着山脚沟地里绿色的日喜村时,她看到了两旁茂密的森林。
那是她梦中那条青龙最后的归宿。
她这才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早已注定,十七岁的次珍在山头呼吸着潮湿的空气,望向山沟里那个村落,相信了命运,也接受了命运。
时间已经到了十点,次珍准备让孙子睡下。终于把因为不让看手机而哭闹的孙子哄睡后,她才又来到佛堂点燃了一盏酥油灯,照例为亡夫祈祷,之后她又特意为成列家的女儿和那个跳下去的尼姑念了一会儿经。躺下后她脑海中又跳出白天的那个问题:跳河是会淹死还是如何?尼姑虽然跳了河却是被摔死的,成列家的女儿跳了河可能是淹死的,而自己的丈夫入了河之前就已经死了,不知道漂到了哪里。次珍想了许久,得出结论:跳河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可能会承受更大的痛苦。
第二天次珍早早地起床打茶、供水,然后叫孙子起床吃饭,送孙子上学,转经,回到安置点晒太阳。卓玛早就到了,次珍远远地看见卓玛在人群中光彩夺目,众人都看着那张小巧的嘴一张一合。卓玛也是从外地嫁到日喜村的,她比次珍大两岁,属虎,今年刚好五十岁。卓玛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次珍是这么想的。卓玛逃过婚、捉过奸、分过户、打过工。如今一人成户,分到了安置点一套最小的户型。卓玛敢说敢干,村里人都敬她三分、畏她三分。但是唯独次珍十分羡慕她,羡慕她敢逃婚、敢分户,羡慕她敢在跳舞时大声唱歌,当然次珍对她有多羡慕就有多嫌弃。次珍和村里所有的女人一样,都觉得她不像个规矩的女人,但是次珍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向她靠近。
去年3·28乡里组织群众跳舞,女儿要在年后出门打工挣钱,于是次珍只能代替女儿去跳弦子舞,还好那只是类似于锅庄的一种慢舞,众人围成一圈,三个拉弦子的男人在前面领舞,边拉边唱,后面的人只需随着旋律边唱边跳。不然如果真像电视中所演那样欢腾,她又怎么可能跳得动。每次到唱歌的部分,排在前面的男人大声歌唱,而排在后面的女人们却不肯开口,领舞的男人多次提醒女人们唱歌,但每次排练,在低沉的男声中,只有一个尖锐的女声,那个就是卓玛。
某一次下午排练,卓玛请假,于是女人的队伍中毫无声息,终于在领舞提了三遍要求之后,次珍鼓起勇气唱了出来。她也希望像卓玛那样瞩目,然而她发现自己喉咙发出的声音与歌曲、舞蹈格格不入,她身边的两个女孩十分惊讶地盯着她,而召集他们排练的村干部则各自聊天、看手机,根本没有人注意她。于是她又闭了嘴,过会儿再响亮地唱两句,随后又闭嘴。
隔壁村的桑吉今天来安置点找亲戚,也在那众人间坐着。卓玛在人群中忿忿不平地对着他说:“有了婚约又怎样,人家又没生孩子,你这臭嘴不要成天胡说八道。”次珍走近时听到卓玛这么说,桑吉则是为显自己更高,便抬了下巴说道:“有了婚约,又嫁到别处,肯定是原先那家不要啊,这不是品行不端正又是什么。”卓玛还想回嘴却看到了已经走到眼前的次珍,于是立刻住了嘴。次珍不知道他们在讨论谁,但是围在那里的人都不说话,有些低着头,有些意味深长地看着她。次珍突然意识到他们肯定在说自己,此刻次珍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一方面因为他们背地讨论自己而生气,另一方面她又因人们在讨论自己而确幸,当然她只能表现出生气,于是次珍白了一眼桑吉便直接回家去了。
回到家中的次珍在脑海里一遍遍骂着桑吉,她想象着自己在人群中指着比自己矮了一头的桑吉进行反击,她妙语连珠、有理有据,而桑吉则低着头哑口无言。众人也将钦佩的目光投向她。如此在脑海中骂了几轮,次珍发现该接孙子放学了,自己连午饭都忘了吃。于是她赶紧就着酥油茶吃了个饼子,然后出发接孩子去了。
晚上外出打工的儿子回来了,次珍看着这个和亡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又因经历了白天的事,临睡时她又陷入了回忆。次珍是在嫁到日喜村的第二年生下的儿子洛松,夫家因为次珍第一胎就生了儿子十分高兴,也给村里经常去次珍娘家所在的乡镇做生意的人捎了口信。但是很快一个传言在日喜村散开,说欧珠家的儿媳在嫁过来之前就有了婚约,还有人说他们家的孩子不是罗布的而是嫁来之前就有了身孕。
那一巴掌扇在次珍脸上时,出嫁前母亲给她的耳环也被甩出了一只,直到在他们搬迁之前收拾整间屋子都没有找到,那是次珍留在日喜村最大的遗憾。次珍第一次对丈夫讲了那个神奇的故事和女活佛的指示,但罗布并不相信,那两年他们夫妻关系十分紧张,幸好罗布是个木讷老实的人,并没有太为难次珍。终于,儿子洛松开始长得越来越像罗布,那双如牛犊的眼睛一闪一闪时,夫妻二人的关系也逐渐缓和了,但是罗布未曾相信她年少时的经历。
丈夫去世之后次珍也想过自己对他有什么感情,或许是搭伙吃饭过日子,又或是自己依附的一个出路,到后来应该是相互关心的亲人。但是次珍从未对罗布产生过十六、七岁时候与次成相处时的那种感觉。次珍的父亲尼玛与次成的父亲向巴是好兄弟,次成大次珍一岁,属兔,二人打小便是玩伴,次成也是次珍坚定的倾听者,次成相信次珍关于龙的梦,他就同兔子一样温柔。在次成十七岁,次珍十六岁那年双方的父亲为儿女们定下婚约,准备第二年秋收之后成婚。那之后次珍每次见到次成都会十分害羞,几日不见就想说许多话,而见到之后次珍又会觉得日子很长、很慢,往后总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但这种感觉次珍未曾对罗布产生过。不同于罗布的木讷,次成能歌善舞,尤其弦子拉得极好。次成经常在村里过节、耍坝子时,将藏装的两个袖子系在腰间,把弦子抵在腰部,右手拉弓,左手摁弦,边拉边唱边跳,他那一头卷发如羊毛般柔和,在人群中格外耀眼。从冰川回来之后,次珍就再没见过次成。
一夜多梦,次珍起床打茶、供水,送孙子。回到安置点的门口时,她才想起家里需要买些白糖,安置点离县中心还有段距离,走过去着实要花些时间。在安置点门口刚好碰见了要去县里开会的村干部旺堆,于是次珍幸运地搭上了他的摩托车。旺堆要去驻村工作队的办公点讨论房屋改造的相关事宜。除去他们这些直接搬到安置点的村民,村里有几户原先就在县里买了地盖了房子。如今县上有什么房屋改造的项目都是那几家沾光,次珍想到这里又是一阵烦心,但是无可奈何。
两人在桥头分开,次珍看着那辆摩托开到了桥上,那块红布就是从此处飘了下去,于是次珍又体验了一道双手忽地一凉的感觉。随后她转身向菜市场走去,买完东西就去广场边的草地上晒了晒太阳,次珍决定今天要好好散个心。如果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次珍决不会在那天往广场迈出半步,后来村干部旺堆也因载了她一程而心有余悸。
在广场,次珍又遇见了桑吉,桑吉在和他们村的一些人聊天,远远看到次珍后就立马提了音量喊道:“又过来找男人了吗?”次珍气愤不已,几日来的郁闷也于此刻爆发:“你个没长个儿的小子,在说什么胡话!”一听这话,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也有人发出嘘声后喊道:“没长个儿的小子,没长个儿的小子。”桑吉见平日里寡言少语的次珍突然厉害了起来,又因在别人面前揭他短处羞愧难当,转而心生怒意地说:“你个不要脸的女人,结婚前就不检点,现在丈夫死了这么多年,自己脸上满是褶子了,你还到处招惹男人,早上我看到你坐在你们村旺堆的摩托车后面了,你要不要脸啊!”
次珍走开了,她没有理会众人的嘲笑和桑吉那副胜利者的嘴脸。她来到广场人工湖边看着湖面发呆。她以为嫁到日喜村后就会与十七岁前的经历告别,她以为搬迁到县里就会与在村里的生活告别,她以为无人相信她传奇的经历的话那一切就仅仅是她的幻觉。但是如今看来四十八岁的她仍旧没有与十七岁的她断绝关联,二十多年前流传在村里的谣言在二十年之后依旧在县里被提起,所以就算无人相信她的故事也不能否认那段经历的真实性。次珍盯着黑乎乎的湖面进行了一次极具深度的思考。她想到女活佛要让她去一个水汽较足的地方,因为她是龙。秋风吹过湖面泛起涟漪,她看到成列家女儿那个活泼的笑脸、那张飞天的红布,还有被哈达裹得严实的罗布。
跳河不稳妥,她想。要在岸边留一个自己的物件,她想。于是在一个平常的上午,她和往常一样来到广场人工湖散心、聊天,直到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藏装的老人将手机放在岸边,随后跨了石栏跳入了湖中。
县里又有了新闻了。
湖水很凉,寒意仿佛要渗透入骨中。水下不完全是黑暗,有微弱的光但很模糊,水进入耳朵让她失去了听觉,或者说因为水下本就无声。水混着沙子进入鼻腔和口腔直抵肺部,刺痛随之而来。次珍闭上眼睛以减少双眼的痛感。她看到了那条青龙一会儿直冲云天,一会儿潜入水中,往复不止……
再有意识的时候她面前是卓玛,卓玛看着十分担心。然后是白色的天花板和刺眼的白光,白色的人又出现在她眼前,摸了摸她的脸,拉了拉她的眼皮。听觉从这个时候开始恢复,有哭声、机器的滴滴声、人的说话声。次珍转动眼球发现旁边有卓玛、医生和警察。她知道现在自己在医院,自己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了。她想说话,但一张口就感觉肺里一阵疼痛,止不住地咳嗽。此刻周边的人都围了过来,眼神中满是关切。医生问她哪里不舒服,警察问她为什么跳湖,卓玛问她为什么轻生。此刻好似众人都要抢她,她平稳了呼吸一个一个回答:“感觉身体很凉、肺疼……协松村的桑吉在众人前污蔑我所以跳了湖……”卓玛在帮她掖被角、理头发,医生在调整氧气管的角度,警察拿着笔记本记她说的话……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到她床前问她怎么回事,次珍认识这个女孩,是日喜村的驻村队员。与她同来的另一个女孩则是看了眼次珍就低着头跟警察说话,那是今年新来的驻村队员,次珍只在发盐的时候见过她一次。随后三个儿女都来到了房中,大女儿在问卓玛情况,小女儿俯身趴在她身侧大哭,儿子站在床边看着她。再然后许多村民也来了,他们围在床边问她为何轻生,现在感觉如何。次珍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他们,疼痛、寒意此刻都已经消散,次珍觉得自己更加精神了。医生让家属带她去拍CT,于是她看到床四周的人们都将手放在床上,转动病床推向门口,而驻村工作队员一人扶着一边门等待着,她看到副乡长站在门外。一个由男女老少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将她推至CT房,而后又推向住院病房。其间孩子们时而落泪,时而关心,村民们有的为她送开水,有的搬东西。
回到病房,护士为她打针输液,测量心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忽然安静下来后,一阵疲惫感侵袭全身,她也尝试放松身体回想整个经过。她并不想死掉,那是十分清楚的。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跳入湖中,那一刻她好似着了魔一般,她好像记起了那些故事和那条青龙。此刻村民们开始聊天,他们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相信那个贫嘴的、恶毒的桑吉污蔑他们村一个善良、清白、老实的女人,而可怜的女人受不住那天大的耻辱,一时想不开跳了湖。人们开始聊到桑吉的家人,又谈论他们家二儿子搞运输,再谈到近年搞运输的收入逐年增加,最后谈到前段时间县里组织村民参加驾驶培训的名额太少。于是次珍终于开始剧烈咳嗽起来,人们立刻停止闲聊看着次珍,问候声此起彼伏。次珍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满屋人的心。这一刻,次珍感到无比的荣耀。
她突然想到,如果此刻跟大家说她十七岁时传奇的经历,人们可能也会相信。而正当她准备说时,屋内众人被护士以病人需要休息为由赶出了病房。她转过头来看了看女儿,发现她和平日一样看起了手机。次珍只能闭上双眼好好休息,她感觉又看见了那条青龙,但是很模糊,很遥远。她脑海中突然忆起那个新来的驻村干部,上次发盐时次珍家少了一人份,新来的那个人用外地方言解释这次每家户主都没有算进去,每家都是少一份的。现在想想一定是他们统计的时候出了差错,下回要像卓玛那样敢于质问到底。想着想着,次珍终于睡了过去。
次珍,女,属龙,十七岁嫁入萨溢乡日喜村欧珠家,给欧珠家儿子罗布当媳妇。十八岁生下儿子,二十四岁生下大女儿,三十岁生下二女儿,四十岁丧夫,四十一岁离村搬迁至县城的安置点,四十八岁本命年时投湖自尽。
未遂。
“你瞎说什么?哭了一天一夜又是谁传出来的。人家家人都说了,找到手机才确认是跳了河。不然人都丢了,又怎么知道在桥洞底下哭了一天一夜?”白玛老头即刻反驳道。
“活该,这种女人就不该活着,不守妇道,丢我们村的脸。”卓玛在一旁吸了口鼻烟说道。
日喜村成列家的女儿在拉萨跳了河,听说是因为生活不检点,染了脏病,所以她羞愧不已,投河自尽了。次珍在集中搬迁安置点门口的凉亭内晒着太阳,听村民们讲这件大事。传消息是男人们的事,卓玛在村里以泼辣闻名,也就她可以在这些男人间插个嘴。
投了河是淹死的还是如何呢?次珍将孙子脱掉的衣服盖在膝盖上,自从搬迁到县城,她膝盖疼的毛病又加重了。县里没有村里那么暖和,搬迁之后他们的房子又被安排在五楼,每天爬楼梯走上几次,她感觉这比在村里走土路、种地还困难。跳河时可能会撞到河边的石头摔死吧?次珍想到这里,那种自小就有、双手忽地一凉的感觉又来了,她没有再想下去。
“上次那个尼姑,跳河的那个尼姑,好像就没有跳到河里去吧?”白玛一边问着一边将目光转向次珍。前几个月的那件大事,次珍是日喜村唯一的目击者,那可是全县的大事。起初日喜村的村民在跟搬迁点其他村的人说这件事时,总会提一句:“我们村洛松家的次珍看见了。”
“可不是吗?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能跳进河里才怪呢!她直接摔在了河边的石滩上,救她的人赶到的时候她还没死透,一直抽搐呢。”不待次珍开口,卓玛又用她尖锐的喉咙说出了次珍当时跟她说的那些话。此时凉亭已经围了不少人,有同村的、有同乡的、也有别乡的,在场的人听卓玛说话时,都将目光投向她,有些敬佩、有些质疑,不过多数是听声音时,习惯性地将眼睛看向声音的来源罢了。然而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卓玛的声音越来越亮,就好似这以红色装饰屋檐、周体通白的楼群是信众一般,而她正是那讲经的喇嘛,神圣无比。次珍看着卓玛的样子,心中并无多少不满,更多的是羡慕。但此时次珍的脑海正被那天飞在空中的红布所占据。
如果不去买那捆白菜,她们定然不会遇见。次珍回想那天早上的情景——她如往常一般,喂孙子吃了饭后就背上孙子的书包,牵着他的手走出搬迁安置点的大门,走向学校。送完孙子准备转向转经路时,她突然记起家里需要买些白菜,于是转身向菜市场走去。“搬迁到县里之后,连白菜都要自己去买。”次珍想起邻居四郎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为什么人家就能说清楚呢?次珍也有过类似的感想,四郎那句话早已在安置点的老人间传开,这句话多简短、真实。她怎么就说不出这种大家都十分认可的话呢?当然这句话并不被年轻一辈认同,村里气候宜人,庄稼果蔬长得也好。但是从县城到村里有三个小时车程,其中两个小时还是翻山的土路,所以年轻人都说县里更方便,打工也好找工作。次珍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她男人去世之后,家里主要是儿子和女儿做主。虽然村里的房子一直都在,但孩子们要住在县里,她便长期跟着一起,负责带孙子。她也会想念村里的生活,女儿说村子海拔比县里低,次珍肯定不知道海拔是什么,女儿也没有解释,但她知道县里更冷、更干,即使她不掌握所谓“海拔”的含义,也能感觉出来。
那天,次珍抄了近道,沿着河边走向菜市场,那条路从县城的大桥下面通过。桥很高,离河面有三十米左右。次珍正考虑除了菜还要买些什么,余光却瞥见空中有一抹红色在飞,确切地说是在桥面与河面之间的空中,有一块红布缓缓飘下,轻轻落在了河对岸的石滩上。后来她尝试着把这件事跟身边人说清楚,但大家都说一个人从高处往下跳怎么可能是那样的,肯定是快速掉下,然后狠狠地砸在石滩上。她无法说服别人,自十七岁时的那件事之后,她便再也没能让任何人从真正意义上相信自己。她也清楚,那个穿着红色僧袍的年轻尼姑掉在河对面之后,身子一阵阵颤动,鲜血从她身下流出,浸入石头的缝隙中。
岸边有人叫了救护车,救护人员到的时候,那块红布还在轻轻飘动。
“好像是因为出嫁后家庭生活不和谐就出家了,她出家后成天郁郁寡欢,最后竟然跑到县里的桥上跳了下去。”隔壁村的巴桑知道一些内幕,于是他成为了继卓玛之后楼群中的另一位“喇嘛”。次珍脑海中还是那块红布,挥之不去,于是她忍着膝盖的疼痛从板凳上站起来,招呼孙子回家。太阳还没有下山,人们依旧在那里坐着,谈论那个跳拉萨河的小媳妇。无人在意次珍的去留,除了卓玛看了她一眼以示告别,倒是小孙子的玩伴们对他依依不舍。
出家,次珍也曾差点出了家。次珍是在十七岁那年嫁到日喜村的,她的老家在县城以南六、七十公里处。出嫁那天,父亲带着她翻了一座山,山路时好时坏,他们时而骑马,时而牵马。到了镇上留宿一宿,次日又赶了一天的路穿了县城,他们才到达了日喜村所属的萨溢乡。夫家的父亲和弟弟在路口迎上他们父女二人,又在乡政府所在的村留宿一宿。第三天四个人又翻了一座山,山路时有时无,他们时而沿路,时而辟路,终于在第三天的傍晚到达了日喜村。十七岁的次珍因为能在第三天就到达出嫁的地方而倍感幸运,因为前两年她的伙伴嫁到了外地,听村里人说那个女孩在路上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她骑了马,坐了车,还渡了河。她十分感激家乡的那位女活佛,如果不是她说次珍要远嫁但不能离开本县,谁知道她要骑多久的马,走多长的路,翻多少的山。
真是曲折离奇的经历啊,次珍想起出嫁之前的事情就很疑惑,为何自己一生的精彩经历都在十七岁之前呢?回到家,次珍开始着手准备晚饭,她想煮一锅挂面,一个月前驻村工作队发的挂面还剩三袋。她弯腰把地上的高压锅拿起放在了灶台上。上了楼之后她膝盖的阵痛一直持续到现在,没有缓解。
说到次珍差点出家这件事,其实还应当讲一讲更久远的事情。次珍的老家在牧区,那里有闻名西藏的冰川,当然“闻名西藏”这件事是她近几年通过抖音才知道的。年少时父亲总跟她说离夏季牧场一天半马程处的地方有雪山和冰川,传说那个地方人迹罕至,有各种神灵鬼怪出没。她还记得在她七岁那年一个冬日的晚上,屋外下着大雪,坐在炉子旁的母亲将她揽入怀中。那时炉子里火烧的噼啪声、窗外的风声和雪落的沙沙声、羊群的咩咩声还有弟弟熟睡的鼻息一齐在房中穿梭。母亲搂紧了次珍,见她迟迟不愿睡下,就讲起了关于冰川的故事。
十几年前的冬天,村里的一个人去冰川所在处寻找走丢的牦牛,到山脚时他因有些害怕眼前白色的世界而不敢向前。正当他准备往回走时,却看到半山腰处有一个移动的黑点,眯眼看去,那物体的前部还有彩色的东西,他想那可能是自家牦牛的彩色项圈,心生狂喜,勇气也随之而来,于是一个人往半山腰处走去。眼前虽是雪原,但太阳仍与雪山并肩。他并不觉得寒冷,甚至因为穿着祖辈留下的羊皮袄爬了许久的山,他越走越热,而那黑点却也同样在移动。幸运的是那黑点走得很慢很慢,离得更近时他发现那确实是一头牦牛,但比他走丢的那头大了许多。他的牦牛在村里十分有名,它壮硕、魁梧。村里老人总说他的牦牛是天庭的护卫下凡,不然怎会如此壮硕。如今竟看到一头更大的,一时间他也愣在了原地,惊诧不已。
只见那牦牛忽地转向他,两角的曲线堪称完美,毛发柔顺如抹了酥油一般。他正想着要不要将这牦牛赶回家,毕竟大概率这也是一头走丢的牦牛。不成想那牦牛突然像疯了一样冲向他,它顺坡而奔,犹如一块巨石从山上滚下,激起雪尘一片。不等他反应过来,双腿早已向山下奔去,可他不慎掉入了一个冰窟中。
所幸冰窟不深,他掉进去之后没有大碍,但是有一只脚崴了。他坐在地上,从冰窟的洞口看向天空,发觉很难凭一己之力到达地面,于是他开始环顾周围的情况,身后是一个大冰块与山连为一体,身前却是一片黑暗。从冰窟的洞口照入的光线只能照亮五米范围内的空间,而他前方的黑暗与他之间还有一块大石头。
正当他考虑是否要往黑暗中走去时,却听见一声极重的喘息声从黑暗中传来,还有一股暖风扑面。他不禁叫出声,一下跌坐在地上——不曾想那黑暗中竟亮起两个黄色的大灯笼,一闪一闪,从黑暗深处逐渐接近他。而那个人只能紧紧靠着身后的冰面,无处逃遁。只见在黑暗与光明交界处,一对巨大的鼻孔闯入阳光中,而后是长长的胡须与鼻梁。他料定这不是什么野兽,那鼻孔大到可以装下两个成年人。因为受惊过度,他在原地怔住了。
终于,那两个一闪一闪的大灯笼离他越来越近,喘息声近在咫尺,热气一阵强过一阵。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女儿,那个龙年出生的女儿如今才十二岁,如果自己丧身于此,他祈祷自己的魂魄可以乘天上的神龙回到女儿的身边。正当那灯笼即将闯入光明时,他听天由命,闭上了双眼。
喘息声在,热气也在,还有一个新的声音——水声,确切地说是放大了许多倍的舔舐声。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仅是十几秒,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是龙,是寺庙壁画上、柱子上经常出现的龙。只见那龙的双角可触至洞口处,而灯笼是龙的一双黄色的眼睛,鼻孔下的龙嘴处有一条鲜红的、宽大的舌头。那龙在舔石头,双眼紧盯着他。他只能张大嘴巴一动不动……随后那龙终于舔完,慢慢将身子缩回,隐入了黑暗中。
他感到十分惊奇,却不敢向前太多,于是他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石头前,学着龙舔了一口石头。就在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到那块石头是温热的,当舌尖碰上石头的一瞬,一股热流传遍周身,他的寒冷与饥饿也随之消散。于是自那天始,每当他感觉饿了,就都会舔一下石头,其余时间就坐在石头旁边。虽然身处冰川之内,洞口也会经常飘进雪花,但他从未觉寒意。那条龙每日都探出头舔几口石头,除此之外,就是隐在黑暗中,好似在睡觉,而他也逐渐习惯了那种鼻息。
但是他始终不知道何时才能脱身,或者在这洞中直到老死。他只能通过洞中日照时间逐渐变长、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逐渐变密来感受时光的流逝。近几天他发现那条龙每次舔完石头都会朝上看看洞外的天,这是他掉下去这么久之后,周围唯一一个变化。他下巴的胡须已经长到喉结的长度了,他渴望变化。终于在一个夜晚,那条龙又探头到了石头处,是那天的第二次。它没有舔石头而是望向了星空,他预感到可能有事即将发生。
此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到了第四天,洞中迎来当天的第一缕阳光之时,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自黑暗深处传来,他马上捂紧耳朵朝黑暗看去——只见那龙如往日般将头探至石头旁张开了大嘴。只不过此次不是舔舐,而是用舌头将那大石头卷入了口中。随后龙头向上朝着洞口伸去,一条金色的身体从他旁边爬过随后伸出洞口,那片片龙鳞闪闪发光,照亮了整个洞穴,他这才发现那洞中四周皆是冰川。而最后龙尾从他身旁经过时,他一把抓住了龙尾,于是整个人立马腾空而起。出了洞口后,他立刻放手,随之顺利地掉到了地面上。抬头望去,只见那条金色的大龙曲着身子,随阵阵雷声直飞入天空的云层中。而当他终于看向周围时,却发现冬日早已过去,春天来了。
故事讲完,次珍也安心睡去,但是那天晚上她梦到了一条青色的龙从雪山顶的空中飞过。梦中她好像是看着青龙的旁观者,又像她自己就是那条龙。飞呀,飞呀,飞过了雪山、湖泊,最后来到了一片森林众多的沟地。她感觉得到青龙留恋雪山,却好似有一股看不见的神力将青龙召唤了过去。
听了故事又做了梦的次珍更想见识一下那个神奇的冰川。次珍也同故事中的女儿一样属龙,所以年幼的她固执地认为那个冰川有龙。当时父母双全,深受宠爱的她毫无畏惧,作为伙伴中的领导者,她一遍遍讲着冰川的故事,让她的伙伴们一度深信,大人口中的那片冰川深处定然盘踞着许多龙。有白色的、黑色的、青色的,最大的那条是金色的,比黄金还灿烂的金色。事实上他们没有见过多少黄金,有的仅是长辈口口声声称之为“黄金”的氧化金属饰品,它们发暗、毫无光泽。但是那时的他们,包括次珍在内,或者说以次珍为代表的他们,有的是精力和想象力,他们可以想象比黄金还灿烂的金色究竟有多耀眼。
但是这种能力在他们真正走进冰川后依次逐渐减弱,并在次珍十七岁那年荡然无存。十七岁那年次珍终于如愿见到了冰川。那年父亲带着日渐能干的女儿来到夏季牧场,而后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早晨带着女儿和同伴一道骑上马向冰川进发,他们要在傍晚时分借宿在那附近的一个村落,这样才能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抵达冰川所在处。于是第二天次珍早早地起床打好了茶,她在洗漱干净之后从怀中掏出了那个有点发黑的金手镯,那是三年前奶奶临终时留给她的嫁妆。她清楚,只有在出嫁时才能戴上手镯,她也明白,今年她就可以戴上手镯嫁入向巴家,嫁给他们家的二儿子次成。
次珍喜欢那个小伙子。
此刻,东方才有些许光亮,她还是决然将手镯戴在了左手手腕处。她觉得进入冰川就好似圆了自己十几年的梦一样,这是个神圣无比的时刻,所以她要戴上最珍贵的东西表达尊重。十年后,她牵着儿子、背着女儿走进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殿时也产生了这种感觉。在翻了一个土坡后,一众人停在山顶远眺,那几座雪山与她小时候梦到青龙的雪山一模一样,她并不觉得惊讶,因为这些年她一直坚信会如此。下了小坡来到雪山旁,父亲与众人在一处平地开始煨桑祈福。她兴奋不已,四处走动,却见一个洞口散着蓝色的光,洞口较窄仅容一人通过。
她不该进去的。
但是来到冰川的次珍又怎么可能是平日里稳重成熟的次珍,她直接走了进去。那是一个左右和顶部都是冰的冰洞,洞内并不像洞口一般狭窄。即使次珍张开双臂,也不能同时碰到两边,而举起手臂、伸伸手指却能碰到洞顶。
洞内无比安静,没有一丝声音,只有蓝色的、寒冷的光。但次珍并不觉冷,冰洞内的温度与外面没有大的差别。次珍不敢用力呼吸,只得站在原地。这就是冰川内部,可能有龙的地方。她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她也有点害怕,不知道前方究竟有什么。
后来次珍回想时,发现那是她此生最后一次自我抉择。
她稳了稳心神,用右手摸了摸手镯,准备原路返回。正在此时,她听见有个声音在叫她,仿佛很远但又十分清晰。她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传来,于是就没有理会,朝着洞口走去。
又是一声,她听得清楚,所以确定那绝对不是幻听,她的双手忽地一凉,脚下加快了速度。第三声从洞内深处传来,她猛地回头——一声惊雷从四周扑向她,随后眼前一黑,毫无知觉。
当她再次醒来时已是三天之后,她发现自己躺在了夏季牧场自家的帐篷中,里面没有其他人。
正当她疑惑之时,父亲请的喇嘛走进了帐篷中,跟在身后的父亲看见女儿醒来,喜出望外,并言真是喇嘛福泽宽厚,一来女儿就醒了。喇嘛问了问次珍整件事情的过程,又闻言次珍以前总梦到青龙在雪山上头,便脸色一沉断言道:“呼唤声、雷声、青龙都是她中了妖魔邪祟的幻术产生的幻觉。冰川本就不是什么吉祥之地,如今又被妖魔伤了身,只能出家当尼姑,了却尘事祈求佛祖庇护。”
听父亲说,当他们准备离开时发现次珍不见踪影,于是大家在四周分头找,终于在一个洞口发现了昏迷的次珍。众人见她一直不醒,又不停在她身上熏香,却也不见效果。最后只能先将她驮回牧场,再就近请个喇嘛看看。幸好第三天的清晨,她自己醒了过来。
直到现在次珍都能记起那个上午:帐篷中挤满了人,她半靠在床上,喇嘛盘腿坐在边上,人们一会儿看喇嘛,一会儿看次珍。刚从昏迷中醒来的她产生了一种在人们心中喇嘛和自己一样重要的感觉。那一刻,次珍感到无比的荣耀。
这就是次珍差点出家的原因。
吃完晚饭后,孙子拿着她的手机看抖音,而她拿着佛珠进入了那间狭小的佛堂。最近她越来越不想跟人说话,对一直在身边的孙子,她向来无话可说,而对偶尔回家的子女她也从没有什么表达欲。相反,她总喜欢回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这几年村里和县里发生了不少事,她要么亲眼看见,要么听人传说。这些只是众多奇闻中的一两个,她本不该过于上心,然而这两件事会在她念经、做饭、打扫卫生和睡觉的时候交替着闯入她的脑海中。总想起成列的女儿倒是可以理解,她丈夫家与成列家是远亲,又因在同一个村子里,所以比近亲还亲近几分。那个女孩是次珍嫁到日喜村的第七年出生的,比她的大女儿大一岁。次珍记得那个女孩也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每天穿着脏衣服跑来跑去,活泼开朗。后来去县里上中学,次珍的大女儿也是。没等那女孩初中毕业,成列一家就搬去了拉萨,女孩也没再上学。当时村里的许多人都十分羡慕成列一家,因为那里离释迦牟尼佛近。
去过拉萨的人都说,在那里生活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就近买,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当时次珍在村里唯一的商铺买一袋米都比县里贵上个五十多块。商家说:“我雇人雇车,走了这么久的山路把东西拉进来,这不得花钱吗?”当时次珍和村里人都不会想到再过个两三年,他们也可以过上那种不用翻山就能买到很多东西的生活。
为什么尼姑也总要进入脑中呢?她不是没见过死人,她的丈夫在成列一家搬到拉萨的第二年病死了。幸好不是什么传染病,不然村里人都不会将他的遗体葬入江中。日喜村离怒江近,盛行水葬,这与次珍老家盛行天葬的习俗有所差别。那天早上,人们用哈达将她的丈夫裹紧,而后放在一个木制担架上运出他们家。按风俗,次珍不能同去,黎明的黑暗中,她目送自己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最后一程,那年她刚好四十岁。
为什么尼姑总进入她的脑海?可能是因为她曾经差点成了尼姑,她想。那她又为什么没有成为尼姑呢?还是得感谢那位女活佛。那年从夏季牧场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着手准备次珍出家的事,他打听到隔壁村的深山处有一座尼姑庵,还有一位十分尊贵的女活佛,于是父亲带着次珍出发了。他们骑马来到尼姑庵所在的山脚处,父女二人又爬了半天的山才到达目的地。途中次珍说:“如果真的在这里出家,往后上山下山得受多少苦啊。”父亲走在前面低头不语。见了女活佛说明缘由,父亲叩拜请求女活佛收下次珍。女活佛年近六十,面目慈祥,看了次珍许久,方才说道:“这女子并非受妖魔所惑,入冰川时好似戴了什么物件,又因本就属龙,那冰川中的神灵误将她认作了出嫁之人了。如今出家解不了这劫数,最好嫁到一个水汽较足的地方,得离开这一带,但也不要嫁太远,需要嫁一个属龙的男子,以解此劫。”次珍没有将手镯的事讲给活佛听,如今竟然如此灵验,父亲也只得谢过活佛,回家着手准备次珍出嫁的事了。
回村后,她企图将这次神奇的经历讲给那些伙伴们听,让他们重新信服冰川有龙这一事实,巩固她作为伙伴们领导者的身份。然而伙伴们都不再相信次珍了,他们说喇嘛都说了次珍是中了妖魔的幻术产生了幻觉,所见所梦都是虚假的。后来回想时,次珍意识到好像就是从那时候起,自己失去了让别人信服的能力,那种能力同伙伴们的想象力一道荡然无存。
父亲说好了媒,要她嫁给萨溢乡日喜村一个和她同岁属龙的小伙子。这一家是次珍的舅舅帮着联系的,原先与向巴家的婚约自然取消了。次珍的父亲登门道歉,向巴家十分善解人意。又过了一个月,父亲算好了吉日带着次珍出发了。他们出发的前一晚下了一夜的小雨,次珍如儿时一般依偎在母亲怀中,哭着哭着就睡去了。而父亲听了一夜的雨,叹了一夜的气。幸运的是雨在第二天他们出门前停了,父亲的脸上终于现出笑容。在路途中的最后一座山顶,看着山脚沟地里绿色的日喜村时,她看到了两旁茂密的森林。
那是她梦中那条青龙最后的归宿。
她这才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早已注定,十七岁的次珍在山头呼吸着潮湿的空气,望向山沟里那个村落,相信了命运,也接受了命运。
时间已经到了十点,次珍准备让孙子睡下。终于把因为不让看手机而哭闹的孙子哄睡后,她才又来到佛堂点燃了一盏酥油灯,照例为亡夫祈祷,之后她又特意为成列家的女儿和那个跳下去的尼姑念了一会儿经。躺下后她脑海中又跳出白天的那个问题:跳河是会淹死还是如何?尼姑虽然跳了河却是被摔死的,成列家的女儿跳了河可能是淹死的,而自己的丈夫入了河之前就已经死了,不知道漂到了哪里。次珍想了许久,得出结论:跳河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可能会承受更大的痛苦。
第二天次珍早早地起床打茶、供水,然后叫孙子起床吃饭,送孙子上学,转经,回到安置点晒太阳。卓玛早就到了,次珍远远地看见卓玛在人群中光彩夺目,众人都看着那张小巧的嘴一张一合。卓玛也是从外地嫁到日喜村的,她比次珍大两岁,属虎,今年刚好五十岁。卓玛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次珍是这么想的。卓玛逃过婚、捉过奸、分过户、打过工。如今一人成户,分到了安置点一套最小的户型。卓玛敢说敢干,村里人都敬她三分、畏她三分。但是唯独次珍十分羡慕她,羡慕她敢逃婚、敢分户,羡慕她敢在跳舞时大声唱歌,当然次珍对她有多羡慕就有多嫌弃。次珍和村里所有的女人一样,都觉得她不像个规矩的女人,但是次珍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向她靠近。
去年3·28乡里组织群众跳舞,女儿要在年后出门打工挣钱,于是次珍只能代替女儿去跳弦子舞,还好那只是类似于锅庄的一种慢舞,众人围成一圈,三个拉弦子的男人在前面领舞,边拉边唱,后面的人只需随着旋律边唱边跳。不然如果真像电视中所演那样欢腾,她又怎么可能跳得动。每次到唱歌的部分,排在前面的男人大声歌唱,而排在后面的女人们却不肯开口,领舞的男人多次提醒女人们唱歌,但每次排练,在低沉的男声中,只有一个尖锐的女声,那个就是卓玛。
某一次下午排练,卓玛请假,于是女人的队伍中毫无声息,终于在领舞提了三遍要求之后,次珍鼓起勇气唱了出来。她也希望像卓玛那样瞩目,然而她发现自己喉咙发出的声音与歌曲、舞蹈格格不入,她身边的两个女孩十分惊讶地盯着她,而召集他们排练的村干部则各自聊天、看手机,根本没有人注意她。于是她又闭了嘴,过会儿再响亮地唱两句,随后又闭嘴。
隔壁村的桑吉今天来安置点找亲戚,也在那众人间坐着。卓玛在人群中忿忿不平地对着他说:“有了婚约又怎样,人家又没生孩子,你这臭嘴不要成天胡说八道。”次珍走近时听到卓玛这么说,桑吉则是为显自己更高,便抬了下巴说道:“有了婚约,又嫁到别处,肯定是原先那家不要啊,这不是品行不端正又是什么。”卓玛还想回嘴却看到了已经走到眼前的次珍,于是立刻住了嘴。次珍不知道他们在讨论谁,但是围在那里的人都不说话,有些低着头,有些意味深长地看着她。次珍突然意识到他们肯定在说自己,此刻次珍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一方面因为他们背地讨论自己而生气,另一方面她又因人们在讨论自己而确幸,当然她只能表现出生气,于是次珍白了一眼桑吉便直接回家去了。
回到家中的次珍在脑海里一遍遍骂着桑吉,她想象着自己在人群中指着比自己矮了一头的桑吉进行反击,她妙语连珠、有理有据,而桑吉则低着头哑口无言。众人也将钦佩的目光投向她。如此在脑海中骂了几轮,次珍发现该接孙子放学了,自己连午饭都忘了吃。于是她赶紧就着酥油茶吃了个饼子,然后出发接孩子去了。
晚上外出打工的儿子回来了,次珍看着这个和亡夫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又因经历了白天的事,临睡时她又陷入了回忆。次珍是在嫁到日喜村的第二年生下的儿子洛松,夫家因为次珍第一胎就生了儿子十分高兴,也给村里经常去次珍娘家所在的乡镇做生意的人捎了口信。但是很快一个传言在日喜村散开,说欧珠家的儿媳在嫁过来之前就有了婚约,还有人说他们家的孩子不是罗布的而是嫁来之前就有了身孕。
那一巴掌扇在次珍脸上时,出嫁前母亲给她的耳环也被甩出了一只,直到在他们搬迁之前收拾整间屋子都没有找到,那是次珍留在日喜村最大的遗憾。次珍第一次对丈夫讲了那个神奇的故事和女活佛的指示,但罗布并不相信,那两年他们夫妻关系十分紧张,幸好罗布是个木讷老实的人,并没有太为难次珍。终于,儿子洛松开始长得越来越像罗布,那双如牛犊的眼睛一闪一闪时,夫妻二人的关系也逐渐缓和了,但是罗布未曾相信她年少时的经历。
丈夫去世之后次珍也想过自己对他有什么感情,或许是搭伙吃饭过日子,又或是自己依附的一个出路,到后来应该是相互关心的亲人。但是次珍从未对罗布产生过十六、七岁时候与次成相处时的那种感觉。次珍的父亲尼玛与次成的父亲向巴是好兄弟,次成大次珍一岁,属兔,二人打小便是玩伴,次成也是次珍坚定的倾听者,次成相信次珍关于龙的梦,他就同兔子一样温柔。在次成十七岁,次珍十六岁那年双方的父亲为儿女们定下婚约,准备第二年秋收之后成婚。那之后次珍每次见到次成都会十分害羞,几日不见就想说许多话,而见到之后次珍又会觉得日子很长、很慢,往后总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但这种感觉次珍未曾对罗布产生过。不同于罗布的木讷,次成能歌善舞,尤其弦子拉得极好。次成经常在村里过节、耍坝子时,将藏装的两个袖子系在腰间,把弦子抵在腰部,右手拉弓,左手摁弦,边拉边唱边跳,他那一头卷发如羊毛般柔和,在人群中格外耀眼。从冰川回来之后,次珍就再没见过次成。
一夜多梦,次珍起床打茶、供水,送孙子。回到安置点的门口时,她才想起家里需要买些白糖,安置点离县中心还有段距离,走过去着实要花些时间。在安置点门口刚好碰见了要去县里开会的村干部旺堆,于是次珍幸运地搭上了他的摩托车。旺堆要去驻村工作队的办公点讨论房屋改造的相关事宜。除去他们这些直接搬到安置点的村民,村里有几户原先就在县里买了地盖了房子。如今县上有什么房屋改造的项目都是那几家沾光,次珍想到这里又是一阵烦心,但是无可奈何。
两人在桥头分开,次珍看着那辆摩托开到了桥上,那块红布就是从此处飘了下去,于是次珍又体验了一道双手忽地一凉的感觉。随后她转身向菜市场走去,买完东西就去广场边的草地上晒了晒太阳,次珍决定今天要好好散个心。如果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次珍决不会在那天往广场迈出半步,后来村干部旺堆也因载了她一程而心有余悸。
在广场,次珍又遇见了桑吉,桑吉在和他们村的一些人聊天,远远看到次珍后就立马提了音量喊道:“又过来找男人了吗?”次珍气愤不已,几日来的郁闷也于此刻爆发:“你个没长个儿的小子,在说什么胡话!”一听这话,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也有人发出嘘声后喊道:“没长个儿的小子,没长个儿的小子。”桑吉见平日里寡言少语的次珍突然厉害了起来,又因在别人面前揭他短处羞愧难当,转而心生怒意地说:“你个不要脸的女人,结婚前就不检点,现在丈夫死了这么多年,自己脸上满是褶子了,你还到处招惹男人,早上我看到你坐在你们村旺堆的摩托车后面了,你要不要脸啊!”
次珍走开了,她没有理会众人的嘲笑和桑吉那副胜利者的嘴脸。她来到广场人工湖边看着湖面发呆。她以为嫁到日喜村后就会与十七岁前的经历告别,她以为搬迁到县里就会与在村里的生活告别,她以为无人相信她传奇的经历的话那一切就仅仅是她的幻觉。但是如今看来四十八岁的她仍旧没有与十七岁的她断绝关联,二十多年前流传在村里的谣言在二十年之后依旧在县里被提起,所以就算无人相信她的故事也不能否认那段经历的真实性。次珍盯着黑乎乎的湖面进行了一次极具深度的思考。她想到女活佛要让她去一个水汽较足的地方,因为她是龙。秋风吹过湖面泛起涟漪,她看到成列家女儿那个活泼的笑脸、那张飞天的红布,还有被哈达裹得严实的罗布。
跳河不稳妥,她想。要在岸边留一个自己的物件,她想。于是在一个平常的上午,她和往常一样来到广场人工湖散心、聊天,直到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藏装的老人将手机放在岸边,随后跨了石栏跳入了湖中。
县里又有了新闻了。
湖水很凉,寒意仿佛要渗透入骨中。水下不完全是黑暗,有微弱的光但很模糊,水进入耳朵让她失去了听觉,或者说因为水下本就无声。水混着沙子进入鼻腔和口腔直抵肺部,刺痛随之而来。次珍闭上眼睛以减少双眼的痛感。她看到了那条青龙一会儿直冲云天,一会儿潜入水中,往复不止……
再有意识的时候她面前是卓玛,卓玛看着十分担心。然后是白色的天花板和刺眼的白光,白色的人又出现在她眼前,摸了摸她的脸,拉了拉她的眼皮。听觉从这个时候开始恢复,有哭声、机器的滴滴声、人的说话声。次珍转动眼球发现旁边有卓玛、医生和警察。她知道现在自己在医院,自己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了。她想说话,但一张口就感觉肺里一阵疼痛,止不住地咳嗽。此刻周边的人都围了过来,眼神中满是关切。医生问她哪里不舒服,警察问她为什么跳湖,卓玛问她为什么轻生。此刻好似众人都要抢她,她平稳了呼吸一个一个回答:“感觉身体很凉、肺疼……协松村的桑吉在众人前污蔑我所以跳了湖……”卓玛在帮她掖被角、理头发,医生在调整氧气管的角度,警察拿着笔记本记她说的话……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到她床前问她怎么回事,次珍认识这个女孩,是日喜村的驻村队员。与她同来的另一个女孩则是看了眼次珍就低着头跟警察说话,那是今年新来的驻村队员,次珍只在发盐的时候见过她一次。随后三个儿女都来到了房中,大女儿在问卓玛情况,小女儿俯身趴在她身侧大哭,儿子站在床边看着她。再然后许多村民也来了,他们围在床边问她为何轻生,现在感觉如何。次珍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他们,疼痛、寒意此刻都已经消散,次珍觉得自己更加精神了。医生让家属带她去拍CT,于是她看到床四周的人们都将手放在床上,转动病床推向门口,而驻村工作队员一人扶着一边门等待着,她看到副乡长站在门外。一个由男女老少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将她推至CT房,而后又推向住院病房。其间孩子们时而落泪,时而关心,村民们有的为她送开水,有的搬东西。
回到病房,护士为她打针输液,测量心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忽然安静下来后,一阵疲惫感侵袭全身,她也尝试放松身体回想整个经过。她并不想死掉,那是十分清楚的。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跳入湖中,那一刻她好似着了魔一般,她好像记起了那些故事和那条青龙。此刻村民们开始聊天,他们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相信那个贫嘴的、恶毒的桑吉污蔑他们村一个善良、清白、老实的女人,而可怜的女人受不住那天大的耻辱,一时想不开跳了湖。人们开始聊到桑吉的家人,又谈论他们家二儿子搞运输,再谈到近年搞运输的收入逐年增加,最后谈到前段时间县里组织村民参加驾驶培训的名额太少。于是次珍终于开始剧烈咳嗽起来,人们立刻停止闲聊看着次珍,问候声此起彼伏。次珍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满屋人的心。这一刻,次珍感到无比的荣耀。
她突然想到,如果此刻跟大家说她十七岁时传奇的经历,人们可能也会相信。而正当她准备说时,屋内众人被护士以病人需要休息为由赶出了病房。她转过头来看了看女儿,发现她和平日一样看起了手机。次珍只能闭上双眼好好休息,她感觉又看见了那条青龙,但是很模糊,很遥远。她脑海中突然忆起那个新来的驻村干部,上次发盐时次珍家少了一人份,新来的那个人用外地方言解释这次每家户主都没有算进去,每家都是少一份的。现在想想一定是他们统计的时候出了差错,下回要像卓玛那样敢于质问到底。想着想着,次珍终于睡了过去。
次珍,女,属龙,十七岁嫁入萨溢乡日喜村欧珠家,给欧珠家儿子罗布当媳妇。十八岁生下儿子,二十四岁生下大女儿,三十岁生下二女儿,四十岁丧夫,四十一岁离村搬迁至县城的安置点,四十八岁本命年时投湖自尽。
未遂。
相关推荐
招聘云藏·藏文搜索引擎藏文数据库录入人员
为了推动藏文信息化建设,海南州藏文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于2013年4月正式启动了藏文搜索引擎系统开发项目,并将 藏文搜索引擎命名为“ཡོངས་འཛིན”,汉文音译为“云藏”,以藏文“ཡོངས་འཛིན”的拉丁转写将其域名名称注册为&l...
2014-03-03 编辑:admin 35844林芝市跻身中国城市品牌评价排行榜全国百强
林芝桃花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每年有桃花节、娘布拉苏节、门巴转山节、贡布节等众多节会。 近日,“2018中国城市大会”在人民日报社举办。根据《品牌评价城市》国家标准和国家部委数据,大会首次对我国地级城市品牌进行了试发布,林芝市以其...
2018-06-05 编辑:admin 22068甘南首届本土歌手广播电视大奖赛颁奖会举办
8月1日晚,在甘肃省合作市甘南大剧院隆重举行首届甘南州本土歌手广播电视大奖赛颁奖晚会曁甘南电视藏语频道全新改版仪式。 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安锦龙,州委副书记、州长赵凌云,州政协主席徐强,中广联少数民族节目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新疆维吾尔自治...
2017-08-04 编辑:admin 25513曲贡,雪域远古的辉煌
由布达拉宫远眺拉萨北郊的曲贡遗址 我对西藏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每当说起高原的人或事,我的思绪就会一下子驰骋到雪域,心中整个地都会为冰峰、羌塘、雅鲁藏布和布达拉所占据,就会想起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日夜夜,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在遥远的雪...
2010-06-18 编辑:admin 25205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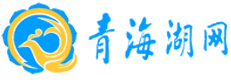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
青公网安备632521020000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