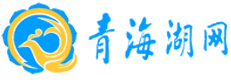生活在青海——收麦天夜晚的田野
作者:轩锡明
来源:青海湖网
时间:2007-11-24 11:32:39
点击数:
17、收麦天夜晚的田野
“温暖的月夜迎着我们飘过来。在银白色河水的尽头,隐约地现出河岸上的草场。高陡的岸上有些黄色的灯火在闪烁,像是被大地捉住的几颗星星。四周的一切都在活动,毫无睡意地颤抖,过着一种安静而又顽强的生活。“这是高尔基的笔下(《人间》)。在俄罗斯文学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阿斯塔菲耶夫……俄罗斯有幸有那么一长串作家,才没有辜负它深邃辽阔、骚动不安而又实在精美绝伦的田园之夜。
中国文学也不乏对田野夜景的描写,如刘真的《长长流水》:“深夜,整个太行山都在静静安睡……风儿不刮了,树叶不响了。天边的月牙儿,好像怕人家把地球偷走了,默默看守着。远处,有一条小瀑布,哗哗哗,日夜不停地往下流,往下流。”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初夏的夜晚,既没了春寒,炎热还要过些日子。西风从渭河上游的平原上,掠过正在扬花灌浆的麦穗,吹了过来。风把白天太阳照晒的热气,都带回晋南和豫西去了。有风的晚上,蚊子顾不得叮人。因为多数稻地没泡上水,蛤蟆的叫声也不到最厉害的时候。”比如刘绍棠对于夜的京郊大运河的专注……
书籍是宝贝,如上生花之笔常常引领我回到少年时代,走进属于我的夜晚的田野。那正是收麦子时节,属盛夏,因为黑黝黝的高山峻岭和暗幽幽的深沟大谷的映衬,我的夜之田野保持着一贯的高原体魄:雄浑犷悍。它粗线条勾勒,大墨块施染,既深沉遥远,又直逼面前。它秉性沉默,很少有蛐蛐歌唱,很少有蛙虫鼓鸣。但它似乎也不乏细腻,同样有小河的闪亮,有流星的划落,有野兽的奔突,有“鬼火”的燃烧,有庄稼和花草飘荡的馨香,有人物也有故事。
少年时代的我,逢暑假必参加夏收劳动。我白天赶牲口驮麦捆子,拾麦穗,傍晚收工的时候又经常会受到生产队长指派,夜里守麦捆子,或放牲口。这样,我便有很多个夜晚是在野外度过。据此,初中二年级我曾写过一篇作文《静静的田野》,受到过老师好评。那作文有对大自然较为真切的感受,败笔是受时代影响地编造了一个时髦的阶级斗争的故事,捉住了一个偷麦捆子的阶级敌人。
收麦天的夜晚,守麦捆子是防盗,放牲口是为了叫它们吃夜草,以补充一整天的消耗,同时防止它们跑失或钻到庄稼地里去。做这些事情大都是大人、孩子相伴,既能照顾更多的大人在家休息好,又能叫孩子们锻炼锻炼。孩子嘛,也天性地喜欢新鲜,喜欢刺激,喜欢到大天地去。
晚饭后,我们夹着铺盖到地里去。
如果是去放牧,实际上是去接替别人,因为役使了一天的牲口收工后就被赶到了取走了麦捆子的茬板地。
日落后的大地是渐渐走向黑暗的。当西山峰巅的天际收敛去最后一抹晚霞,夜的帷幕很快就厚重起来,最后成为一切的背景。在这背景下有高高的白杨树,有码成一垛一垛的麦捆子,有待割的成片的麦田。那些缓缓游动的影子,是马啊、骡子啊、驴啊,它们都在加紧啃啮,因此传来持续不断的嚓嚓声。这嚓嚓声会叫人心疼:呀,是不是白天只知叫它们干活,饿坏了它们……
我们把铺盖安置好,把牲口赶得离庄稼远一点,便不约而同地向一处汇拢来。
守麦和放牧人的前半夜是有许多活动的,说笑话,讲故事,逗趣打闹,也偷瓜吃。白天的燥热消退了,现在是满川清凉;收割的疲乏过去了,现在又恢复了体力,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快乐。
我们最常做、最叫好的是烧地锅锅:在地上挖一个灶炕,灶坑上用土坷垃垒成一个中空的小塔,然后在灶坑里烧火。过一会儿,烧到时候了,把弄来的洋芋填进灶炕,把已经烧红了的土坷垃砸碎,用它们把洋芋严严埋起来。之后那也许是过了半个小时,也许是半个小时还多一点,有一种香味开始弥漫,这时候守夜的人就有好吃的了!这样烧熟的洋芋,口味与水锅里蒸出来的大不相同,散发发的,面面的,真正香喷喷的,平日难得。
烧地锅锅的活儿都是小孩子们干,主谋的大人只是指挥指挥:某某你去挖锅灶,某某你去拣柴火,某某你去挖洋芋,某某你……我们四散跑开,个个雀跃,会是夜色里最生动的表现。
烧地锅锅哩,黑暗中一蓬红火跳闪着,跳闪着,你想象,远远望去那该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诱人啊!因为火光招眼,所以会招引更远地方的、并不怎么相熟的守夜人跑过来。他们钻进人堆,并不说什么,只管嘻笑着抓取洋芋,一点也不客气。在昏黑中我们甚至看不清来人的鼻眼,但能感觉到他们满脸是笑。我纳闷,他们为什么烧火的时候不来,而正好赶上我们吃呢?他们是能闻到熟透了的洋芋味吗?实际上,我们也跑去吃过别人的,情形都一样。
待吃过了洋芋,或吃过了偷来的西瓜,夜也就深了,守捆子的,放牲口的,我们开始散去,该睡的都去各自负责的地界上睡。我们都是席地而卧,顶多往地上铺一块毡片。而在那疙疙瘩瘩的大地床铺上,因为白天的劳累,我们睡着世上最最香甜的觉,任什么华屋和宝榻也取代不了。
今夜我和永福阿哥睡在一起,躺下好一会儿他坐起来,却斜靠在做为枕头的麦捆子上发愣。
“西明,你睡着了吗?”
他摇摇我,我含混道:
“我……我醒了。”
“我给你唱少年吧?”
“你……你唱。”
他就唱,先唱的是:
羊毛摞满三间里,
哪一天捻成线哩?
想尕妹想得眼酸哩,
哪一日才见个面哩?
他嗓门压得很低,也许只有我们俩能够听见,但还是很悠扬徘徊的,一点也不省去什么。
那天夜里他一唱就收不住,一支接一支唱了好长时间,只是这中间有他一些停顿不语的时候,好像是心事压着他唱不出来,要运运气。他唱着,叫我处在似睡似醒的状态,并不好受迷迷糊糊的,他老使我想到他不幸的恋爱。听母亲与别人聊到,他与村东头的冬花姑娘相好,有两年了,想结婚呢,但是姑娘的大大、妈妈不允。那父母不允的原因有点怪,说他读过几年书,但不能出去工作,铜里不去,铁里不来,当农民他以后能活下个人吗?
永福哥唱着,我听着,后来还是睡着了。
这天前大半夜没有月亮,后半夜残月升起来,微弱月光还是使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山峰都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但像蒙着一块硕大无朋的薄纱。在这薄纱下的任何一个具体形象,要么令人不着边际地遐想,要么令人缩头缩脑地心虚。大多数牲口都吃饱了吧,都卧着。望过去,那安祥的样子特别溶入这夜,使人想到它们也会有自己的梦乡。天地是因为吸足了夜晚的湿气吧,显得更加滞重和静谧了。偶尔传来几声牲口卜卜的响鼻,格外地入人耳窝,叫我们在慵懒和困倦之中,心田又滋生一种不经意的轻松和喜悦。
气温像骤然降了下来,我是被冻醒的。
醒后发现永福哥不在,我便极力回想睡死前的情形,想起他好像对我说过:“你躺着,我要去一下,去去就回来……”这阵子我想道,他是去找冬花姑娘了吧?
我回想他唱过的“少年”,有一支唱道:
风不刮时树不摇,
露水在草尖上哩;
你不丢时我不舍,
死活在你身上哩。
“死活在你身上哩”,永福哥唱得我心里沉重,还有什么莫名的担心。我还不到太懂男女情爱的年龄,但是我能明白他不好受,因此也流露出一种“残忍”。他的歌唱好像使夜的脸色都变得忧伤了呢,你看它在云彩飘过月亮的时候阴沉了多少。
我再难以睡着,半支身体,斜躺着向没有根底的远方望去。永福哥去了会怎么样呢……这加深了我对夜的隐秘性的认识。它隐秘,它也真实呢,因为这永福哥才唱了那么多支“少年”,才去找了他的冬花姑娘……
这个时节的田野很勤快,每天都是早早苏醒,这阵儿我们守夜人虽然还懒懒地打着哈欠呢,上早工的人们却已经走出村子,提着镰刀到了地里。我特别注意到永福阿哥,他正在渠边哗哗地撩水洗脸,一边大声喊我们起来,也准备干活。而这时候虚空中仍有不薄的暗影,天上剩余的许多星星跳跳闪闪地不能隐去。有两只百灵鸟从树丛中飞起来,又落下去,是犹豫着该不该开始嗓子晨练呢。
就是这样,反正经过了一夜的休整,不管你缓过来了还是没缓过来,你总得在新的一天里再干活儿。呀!你看哪,怎么一夜间那待收的麦子就黄焦了呢……我们,还有我们亲密的伙伴,马啊,骡子啊,尕毛驴啊,我们总得下大力气苦挣光阴……
“温暖的月夜迎着我们飘过来。在银白色河水的尽头,隐约地现出河岸上的草场。高陡的岸上有些黄色的灯火在闪烁,像是被大地捉住的几颗星星。四周的一切都在活动,毫无睡意地颤抖,过着一种安静而又顽强的生活。“这是高尔基的笔下(《人间》)。在俄罗斯文学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阿斯塔菲耶夫……俄罗斯有幸有那么一长串作家,才没有辜负它深邃辽阔、骚动不安而又实在精美绝伦的田园之夜。
中国文学也不乏对田野夜景的描写,如刘真的《长长流水》:“深夜,整个太行山都在静静安睡……风儿不刮了,树叶不响了。天边的月牙儿,好像怕人家把地球偷走了,默默看守着。远处,有一条小瀑布,哗哗哗,日夜不停地往下流,往下流。”比如柳青的《创业史》:“初夏的夜晚,既没了春寒,炎热还要过些日子。西风从渭河上游的平原上,掠过正在扬花灌浆的麦穗,吹了过来。风把白天太阳照晒的热气,都带回晋南和豫西去了。有风的晚上,蚊子顾不得叮人。因为多数稻地没泡上水,蛤蟆的叫声也不到最厉害的时候。”比如刘绍棠对于夜的京郊大运河的专注……
书籍是宝贝,如上生花之笔常常引领我回到少年时代,走进属于我的夜晚的田野。那正是收麦子时节,属盛夏,因为黑黝黝的高山峻岭和暗幽幽的深沟大谷的映衬,我的夜之田野保持着一贯的高原体魄:雄浑犷悍。它粗线条勾勒,大墨块施染,既深沉遥远,又直逼面前。它秉性沉默,很少有蛐蛐歌唱,很少有蛙虫鼓鸣。但它似乎也不乏细腻,同样有小河的闪亮,有流星的划落,有野兽的奔突,有“鬼火”的燃烧,有庄稼和花草飘荡的馨香,有人物也有故事。
少年时代的我,逢暑假必参加夏收劳动。我白天赶牲口驮麦捆子,拾麦穗,傍晚收工的时候又经常会受到生产队长指派,夜里守麦捆子,或放牲口。这样,我便有很多个夜晚是在野外度过。据此,初中二年级我曾写过一篇作文《静静的田野》,受到过老师好评。那作文有对大自然较为真切的感受,败笔是受时代影响地编造了一个时髦的阶级斗争的故事,捉住了一个偷麦捆子的阶级敌人。
收麦天的夜晚,守麦捆子是防盗,放牲口是为了叫它们吃夜草,以补充一整天的消耗,同时防止它们跑失或钻到庄稼地里去。做这些事情大都是大人、孩子相伴,既能照顾更多的大人在家休息好,又能叫孩子们锻炼锻炼。孩子嘛,也天性地喜欢新鲜,喜欢刺激,喜欢到大天地去。
晚饭后,我们夹着铺盖到地里去。
如果是去放牧,实际上是去接替别人,因为役使了一天的牲口收工后就被赶到了取走了麦捆子的茬板地。
日落后的大地是渐渐走向黑暗的。当西山峰巅的天际收敛去最后一抹晚霞,夜的帷幕很快就厚重起来,最后成为一切的背景。在这背景下有高高的白杨树,有码成一垛一垛的麦捆子,有待割的成片的麦田。那些缓缓游动的影子,是马啊、骡子啊、驴啊,它们都在加紧啃啮,因此传来持续不断的嚓嚓声。这嚓嚓声会叫人心疼:呀,是不是白天只知叫它们干活,饿坏了它们……
我们把铺盖安置好,把牲口赶得离庄稼远一点,便不约而同地向一处汇拢来。
守麦和放牧人的前半夜是有许多活动的,说笑话,讲故事,逗趣打闹,也偷瓜吃。白天的燥热消退了,现在是满川清凉;收割的疲乏过去了,现在又恢复了体力,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快乐。
我们最常做、最叫好的是烧地锅锅:在地上挖一个灶炕,灶坑上用土坷垃垒成一个中空的小塔,然后在灶坑里烧火。过一会儿,烧到时候了,把弄来的洋芋填进灶炕,把已经烧红了的土坷垃砸碎,用它们把洋芋严严埋起来。之后那也许是过了半个小时,也许是半个小时还多一点,有一种香味开始弥漫,这时候守夜的人就有好吃的了!这样烧熟的洋芋,口味与水锅里蒸出来的大不相同,散发发的,面面的,真正香喷喷的,平日难得。
烧地锅锅的活儿都是小孩子们干,主谋的大人只是指挥指挥:某某你去挖锅灶,某某你去拣柴火,某某你去挖洋芋,某某你……我们四散跑开,个个雀跃,会是夜色里最生动的表现。
烧地锅锅哩,黑暗中一蓬红火跳闪着,跳闪着,你想象,远远望去那该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诱人啊!因为火光招眼,所以会招引更远地方的、并不怎么相熟的守夜人跑过来。他们钻进人堆,并不说什么,只管嘻笑着抓取洋芋,一点也不客气。在昏黑中我们甚至看不清来人的鼻眼,但能感觉到他们满脸是笑。我纳闷,他们为什么烧火的时候不来,而正好赶上我们吃呢?他们是能闻到熟透了的洋芋味吗?实际上,我们也跑去吃过别人的,情形都一样。
待吃过了洋芋,或吃过了偷来的西瓜,夜也就深了,守捆子的,放牲口的,我们开始散去,该睡的都去各自负责的地界上睡。我们都是席地而卧,顶多往地上铺一块毡片。而在那疙疙瘩瘩的大地床铺上,因为白天的劳累,我们睡着世上最最香甜的觉,任什么华屋和宝榻也取代不了。
今夜我和永福阿哥睡在一起,躺下好一会儿他坐起来,却斜靠在做为枕头的麦捆子上发愣。
“西明,你睡着了吗?”
他摇摇我,我含混道:
“我……我醒了。”
“我给你唱少年吧?”
“你……你唱。”
他就唱,先唱的是:
羊毛摞满三间里,
哪一天捻成线哩?
想尕妹想得眼酸哩,
哪一日才见个面哩?
他嗓门压得很低,也许只有我们俩能够听见,但还是很悠扬徘徊的,一点也不省去什么。
那天夜里他一唱就收不住,一支接一支唱了好长时间,只是这中间有他一些停顿不语的时候,好像是心事压着他唱不出来,要运运气。他唱着,叫我处在似睡似醒的状态,并不好受迷迷糊糊的,他老使我想到他不幸的恋爱。听母亲与别人聊到,他与村东头的冬花姑娘相好,有两年了,想结婚呢,但是姑娘的大大、妈妈不允。那父母不允的原因有点怪,说他读过几年书,但不能出去工作,铜里不去,铁里不来,当农民他以后能活下个人吗?
永福哥唱着,我听着,后来还是睡着了。
这天前大半夜没有月亮,后半夜残月升起来,微弱月光还是使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山峰都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但像蒙着一块硕大无朋的薄纱。在这薄纱下的任何一个具体形象,要么令人不着边际地遐想,要么令人缩头缩脑地心虚。大多数牲口都吃饱了吧,都卧着。望过去,那安祥的样子特别溶入这夜,使人想到它们也会有自己的梦乡。天地是因为吸足了夜晚的湿气吧,显得更加滞重和静谧了。偶尔传来几声牲口卜卜的响鼻,格外地入人耳窝,叫我们在慵懒和困倦之中,心田又滋生一种不经意的轻松和喜悦。
气温像骤然降了下来,我是被冻醒的。
醒后发现永福哥不在,我便极力回想睡死前的情形,想起他好像对我说过:“你躺着,我要去一下,去去就回来……”这阵子我想道,他是去找冬花姑娘了吧?
我回想他唱过的“少年”,有一支唱道:
风不刮时树不摇,
露水在草尖上哩;
你不丢时我不舍,
死活在你身上哩。
“死活在你身上哩”,永福哥唱得我心里沉重,还有什么莫名的担心。我还不到太懂男女情爱的年龄,但是我能明白他不好受,因此也流露出一种“残忍”。他的歌唱好像使夜的脸色都变得忧伤了呢,你看它在云彩飘过月亮的时候阴沉了多少。
我再难以睡着,半支身体,斜躺着向没有根底的远方望去。永福哥去了会怎么样呢……这加深了我对夜的隐秘性的认识。它隐秘,它也真实呢,因为这永福哥才唱了那么多支“少年”,才去找了他的冬花姑娘……
这个时节的田野很勤快,每天都是早早苏醒,这阵儿我们守夜人虽然还懒懒地打着哈欠呢,上早工的人们却已经走出村子,提着镰刀到了地里。我特别注意到永福阿哥,他正在渠边哗哗地撩水洗脸,一边大声喊我们起来,也准备干活。而这时候虚空中仍有不薄的暗影,天上剩余的许多星星跳跳闪闪地不能隐去。有两只百灵鸟从树丛中飞起来,又落下去,是犹豫着该不该开始嗓子晨练呢。
就是这样,反正经过了一夜的休整,不管你缓过来了还是没缓过来,你总得在新的一天里再干活儿。呀!你看哪,怎么一夜间那待收的麦子就黄焦了呢……我们,还有我们亲密的伙伴,马啊,骡子啊,尕毛驴啊,我们总得下大力气苦挣光阴……
相关推荐
逾十万信徒参加“色拉崩钦”宗教节
31岁的藏族商人扎次从2日晚上23时便前往色拉寺排队。“因为每年一次的这个宗教活动,将会有无数的信徒前来朝拜,如不早点去排队,可能明天下午我们才能朝拜到金刚杵,”他说。 2月2日12点50分,色拉寺一年一度的“色拉崩钦”宗教节开始。这个仅仅持续24个小时的宗教活动,信...
2008-02-13 编辑:admin 6036诗:春天羊群会回来的
那一年 风在冬天的草原走过 芨芨草在舞蹈 大地抓不住一丝喧嚣 雪是寂寞的语言 谱写着苍白而单调的音符 音符是一堆堆...
2011-11-14 编辑:admin 5559海南州组队参加青海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7月5日,青海省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举行,运动会将于8日全面结束。迷人的金银滩开满着美丽的格桑花,圣洁的青海湖碧波荡漾,来自青海省内各州、地、市、县的上千名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以及慕名而来的省内外宾朋欢聚一堂,和草原...
2009-07-06 编辑:admin 4533共和县德吉滩扩建项目
一、项目概况:项目区位于共和县恰卜恰镇德吉滩,距恰卜恰镇2公里,在省道214线沿线。主要扩建大经堂、转经房、班禅纪念塔,路南修建藏族服饰表演厅、赛马场、民族传统射箭场等项目及配套服务设施。二、经济效益: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年各类收入达630万元,投资回收期3.2年三、产...
2008-05-29 编辑:admin 8421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