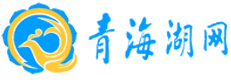永基卓玛小说:《扎西的月光》
作者:永基卓玛
来源:青海湖网
时间:2009-12-07 11:15:45
点击数:

作者简介:永基卓玛,藏族,一九七九年生于云南迪庆,一九九六年就职于云南省迪庆州歌舞团。琵琶演奏。二○○六年开始创作,作品散见于《边疆文学》、《民族文学》、《西藏文学》等文学刊物。散文诗《雨的音韵》入选《中国二○○六散文诗精选》。现供职于云南省迪庆日报社。
扎西的月光
“一定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穷得叮当响的鬼地方。”在心里反复叨念着这句话的扎西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下了决心,从家里出发。
这个时候,天才刚开始透亮,太阳还没出来,藏在半山腰的永格村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村里的人都还没起床,那一声声鸡鸣在雾中清晰地响亮着。
临走之前,扎西环视自己居住了二十年的老屋,屋子因为年久失修,像一个衰老的老人立在那里,全身发出衰败之气。“终于要离开这里了。”扎西已经被这股衰败之气熏得头晕眼花,他讨厌这个地方,虽然他就在这里出生,可他还是讨厌这个地方,讨厌这里成天臭烘烘的牛粪味,讨厌这里随处可踩到的羊屎疙瘩,讨厌这里有那么多传说,而这里的人除了沉湎于曾有的传说中的辉煌天天喝酒,就不想想能干点其它的什么。
扎西的父母去拉萨朝拜了,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可一点消息都还没有。
这个早晨扎西可不想遇到什么人。永格有个奇怪的习俗,除了去圣地拉萨朝拜,谁也不能想什么理由来离开这个村子,因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知道了,总会出来阻挠,如果阻挠不成功,则通过其它多种渠道来施加压力。扎西从记事开始就发现村里没一个离开的。而那些去朝拜圣地的人,总会面黄肌瘦地回到村里,回到村里的人从不讨论朝圣途中遇到的事情,也不讨论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日子依然和从前一样。只是一些男人在酒醉后开始吟唱“古老的八角街上,窗户比门还多,窗户里的姑娘们,骨头比肉还软”。
想到这首歌,扎西的心里就有个东西在骚动不安,他一直不理解这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但总觉得这歌词给人无限的向往。
“会见到的。还有很多没见过的东西也会看到的。”扎西真忍不住要把这句话喊出来,可他不敢,这会儿,他不想别人看到他,这感觉真让人激动而又压抑。
扎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清晨的雾气,觉得心里有个东西快要奔突出来。而脚上也像长了翅膀,要飞起来一样。
“哎哟!”扎西的大脚趾碰在一块尖石上,扎西忍不住张开嘴吸着丝丝的冷气,他弯下腰去用手捂住脚,看到自己那双已经破烂不堪的黄胶鞋此时开了个大口子,而那块撞到脚的石块,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经文。“又是那个臭老头干的。”扎西说的臭老头是曲珍的爸爸——多吉老人。
多吉老人是个会飞的人。从小扎西就听别人这么说,可谁也没见过多吉老人飞起来过。这个老人平时沉默寡言,一有时间就拿着石板刻藏经,或者东挖挖,西挖挖。总有些“宝贝”被他挖出来,那些宝贝,不外乎是些写着经文的石块,村里的老人说,是他事先藏好了哄人的。
多吉老人一人带着女儿曲珍,曲珍也像老人一样沉默寡言。
多吉老人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头一个高高的小山包上,俯视着永格这个小山村,只要是在村里,任何一家都能看到多吉老人的房子。多吉老人平时也不多和村里的人来往,像他的房子一样,高傲而又孤独地存在于村民的记忆中。永格总的也就有二十多户人家,七零八落的房子架在山腰的一个小山洼中。
扎西什么都没带,未来总是美好的,干嘛还要带上一些破东西呢。扎西的家里,每一件东西他熟悉得闭上眼睛都不会拿错,而且也没什么能让他带走的东西。
想到村里的老人发现他出走,想到父母回到家找不到他时的表情,扎西心里不由一阵阵兴奋。这群老家伙,一个个呆如木鸡,肯定只能吹胡子。
村里唯一让扎西放不下的人还是曲珍。想到时常喜欢沉默,一整天都没有一句话,那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从不正眼看别人的曲珍,扎西那躁动不安的心一下下被说不清楚的缕缕思绪勾住。
“不知道曲珍知道我走了,会怎么想。”扎西不由这么想,“当我有了好日子过,我就回来找曲珍。”这么一想,扎西就觉得对曲珍有交代了。
“曲珍,你等着我过好了,就回来了。”
脚上大拇指丝丝地扯着心口疼,扎西一瘸一瘸地走着。怎么刚出门就遇到这样的事。他不由连连吐口水。“我应该像羚羊过山冈一样走出村子才对。”扎西不由在心里嘀咕着。都怪这个老头,难道说他有什么法术?等会儿经过他的房子时,一定要对着他的房子吐口水,才能去晦气。
酝集着一泡口水,扎西快到多吉老人的房前了。
刚要把那积攒了好一会儿的口水吐在多吉老人房子的墙根脚,扎西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多吉老人和女儿曲珍正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一位身着艳丽服装的女人,女人身上还背着一个热巴鼓,腰间拴着金色丝带,脚上还戴着铃铛。
曲珍怎么那么小了,好像才十岁的样子,被多吉老人牵着手站在门口。扎西的一泡口水硬是没吐出来。这个女人好像是曲珍的母亲,怎么会在这里,曲珍怎么变小了。扎西还记得小时候见过的曲珍的母亲——她丝毫没有女主人的味道,却像一个客人,什么都不做,经常坐在火塘边哼着歌,还喝酒。村里从来没有女人像这样的。喝酒后的曲珍的母亲坐在火塘边还是哼着歌,她的那些歌,从来没有人能听懂。
但这会儿,戴上脚铃和系着金丝腰带的女人却全身都散发着一股光彩,多吉老人和他那房子被这光彩照出腐朽的气息。他们三个人谁都没发现旁边的扎西。
曲珍的母亲整理过背上的热巴鼓后,就转身大踏步向前走。多吉老人站在后面大声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明年回就明年回,想后年回就后年回。”踏着脚铃声,曲珍的母亲越走越远。
曲珍只是张着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还是谁都没看到扎西,扎西好像隔着一个东西看着这一切。
“我也要赶紧走。”他追向曲珍的母亲,只听到铃铛声越来越远,山路上只是扎西一个人。
永格离扎西也越来越远,被扎西远远地抛在身后。
太阳慢慢出来,在光秃秃的大山间游荡,大山一座连着一座,山底下的那条江依然静静地流淌,没有一点点绿色的大山看上去一片死寂,只有游荡的太阳发出刺眼的光芒。
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扎西已经晕头晕脑。从早上出来到现在,他没吃过一点东西,浑身上下,像他的肚子一样空空荡荡。扎西甩着两只手奋力走着,风在他的脚下软软地飘……
终于,看见公路了。
看着向远方延伸的公路,扎西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未来,在远方吗?未来,想到这个词,扎西觉得像他此时的肚子一样,更加空空荡荡。
“拖,拖,拖……”一辆拖拉机远远过来了。
一群男女兴高采烈地坐在上面。
“年轻人,要去哪里?”车上有人问扎西了。
“我……”
车上戴着红头帕的女人们笑开了。
扎西清了清嗓子,用手指着远方,大声地对车上的人喊到:“我要去那边。
“年轻人,上车吧。”车上的人热情地叫着扎西。
扎西歪着头想想,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便跳上了拖拉机的车厢。
“挤到我了。”“过去一点。”扎西才发现,车厢很拥挤。他想缩到一个地方,却又踩到另一个人的脚。
“稳住了,出发了。”开车的人吆喝着。
“拖……拖……拖……”拖拉机发动了,车厢里站的人又开始嚷嚷起来。一股汗臭和灰尘味很刺鼻地包围着扎西。他看着车子在路上扬起的灰,暗暗在心里说着:“再见,永格。”
还没来得及伤感,车上有个人起头唱起了歌,一车人都跟着唱起来。“呵,藏歌都是一样的。”这些人扎西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唱的藏歌扎西可是熟悉得很。刚刚在扎西心里泛起的伤感立马被歌声挤跑了。
“过来这边一点。”一个戴红头帕的女孩轻轻拉着扎西的衣角说,扎西靠着她站了过去,这是个好位置,能扶到车厢的边上,一下稳住了。扎西对这个女孩感激地笑了笑。女孩却把脸别过去了,只把一个红头帕留在扎西的眼前。
一路上,扎西慢慢和同车的人熟悉了。原来大家一样,都是住在藏在大山中的村子里。路上休息时,那个带红头帕的女孩还把带着的糌粑给扎西吃。在交谈中扎西知道了女孩叫达娃。
“你为什么要出来呢?”扎西问达娃。
达娃抓了抓头,想了半天才说:“我也不知道,人人都在走,都说外面好,我就来了。”由于达娃给扎西让位子,还把东西分给扎西吃,无形中,扎西和达娃慢慢熟悉起来。
黄昏的时候,拖拉机到城里了。太阳的余晖中,一个土黄色的小城就在那里。本来兴高采烈的一车人现在却一个都不说话了。大家都瞪着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
“拉萨?”扎西忍不住问。
司机“呸”了一声,说:“这是县城。拉萨离这里还有好几千公里呢。”
几千公里,听到这个距离。有人伸了伸舌头。
街上不是很热闹,有几头牦牛悠闲地逛在路中央,被它们挡住的车一声接一声的喇叭响起来,它们才甩甩尾巴慢腾腾地走开。
拖拉机带着一车人驶进城里。在一个施工地点停住了,全车的人都跳下来。
扎西这个时候才觉得身子快散架了。师傅过来收钱了。扎西什么都没有。达娃大概已经知道了扎西肯定没钱,帮扎西付过车钱,问:“你要去什么地方?”扎西摇着头,说:“不知道。”
这个时候,师傅大声说话了:“大家没地方去的,可以去这里做活。”他指着正在盖建的大楼说。
达娃望了望扎西,好像是在问扎西去不去。
扎西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两个人笑了笑,一群人又跟着师傅走。果然,有地方可以住,还有吃的东西了。
达娃在工地里负责做饭,而扎西,要跟着好多工人一起挑石头水泥。
扎西就这样在这个土黄色的小城安顿下来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扎西和达娃一直在工地上做活。一个地方的工程做完了,他们跟着别人又搬到另一个地方开始。一栋栋新房子建了起来,扎西每看到这些新房子时,心里就有了一点念头,我在为这个城市建设呢。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自豪感。
一天,达娃约扎西去看电影。
收工后,两人换了干净衣服来到电影院。心里想:我们也是城市人了。
电影院前,两人相互笑望着对方。扎西还特意买了两碗炒葵瓜子把口袋装得满满的。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瓜子,这就是城市人的生活。扎西心里高兴坏了,自己怎么这么聪明。
扎西和达娃已经来看过好几次电影了。虽然电影票有点贵,但两个人几个月就会来一次,电影里那么多稀奇的东西。多好看啊。
这一天放的是一部功夫片,李连杰在里面出神的武功让扎西看得惊叹不已,当李连杰被别人打败时,扎西跟着沮丧,当李连杰又打赢别人时,扎西跟着连连叫好。
“乡巴佬别叫了。”终于旁边有人叫出比扎西的嗓门更大的声音,扎西不知道是对着他喊的,仍然跟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大叫着。“真过瘾!”他还得意地看了看达娃。
却不想达娃拉了拉他的衣服说:“别叫了,人家都在说你了。”
“我?”扎西奇怪了。“看电影就应该这样看嘛,我们村里谁家结婚时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时不就这样吗?”
“乡巴佬,再叫把你赶出去。”这时,查票的过来了。
电影里的场面依然很精彩,但扎西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滋味了。达娃也感觉到扎西的不适,对他耸耸肩说:“管他们呢,自己看自己的。”
还没等到电影结束,扎西就把达娃拉出了电影院。电影院斜对面的歌舞厅正热火朝天地响着舞曲,几个从里面出来的漂亮姑娘很不屑地从扎西和达娃身边走过,留下一股刺鼻的香粉味。
“你说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人么?”扎西忍不住问达娃。
“我们生活在这里啊。”达娃很疑惑地看着扎西。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底算是哪里的人?”扎西忽然感觉有些说不清楚的东西。
达娃不知道怎么接口,便像城里人一样挽着扎西的胳膊,说:“我们回去吧。”
电影院里还传出打斗的声音,月亮亮晃晃地挂在天上,扎西看着地上的影子,忽然一种茫然占据他的心,空捞捞的。
这个晚上,扎西失眠了。他想起以前在村子里时,碰到谁家结婚时,或者村里人聚在一起,总是大声地笑,大声地说,多么快乐。
一连好几天,他都没去找达娃。默默地在工地做着自己的活,达娃感觉到扎西的异样了。她知道扎西肯定还在为那个晚上被别人说了而在生气。
吃过晚饭,她把自己的脸洗得干干净净,还偷偷抹上一点同伴的雪花膏,去找扎西。
果然,扎西一个人在宿舍里。几十人打通铺睡的宿舍里,什么味道都有,又脏又乱,达娃捂着鼻子坐到扎西旁边。
扎西看了看达娃,没说话。
达娃拉扯着扎西:“出去逛逛。”
扎西极不情愿地跟着达娃出了工地的宿舍,路上遇到几个工友挤眉弄眼地对着他们嚷嚷。达娃却是大大方方地拉着扎西的手。
一路上,扎西一直没说话。
达娃可不喜欢这样沉默的气氛,她在心里暗暗懊悔着那雪花膏是不是白用了,怎么扎西一眼都不看她。
两人慢慢走到那池河边,河水无声地慢慢流着。扎西和达娃坐在河边的草地上。“我这几天总在想,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我要到哪儿去,我该做什么?”
达娃听着扎西说的话,忽然感到很陌生:“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有吃的,有住的,我们的工钱还不少呢,我们已经在城里生活了。慢慢地,我们会变成城里人的。”达娃越说越开心。
“我这几天特别想家,出来以后,从未这么想过。”扎西低着头闷闷地说。
“谁都会想家的。哎,我给你唱歌吧。”达娃的声音很好听,甜甜的,脆脆的。“高高的雪山像弯弯的神弓,下山的牦牛像飞射的神箭……”
在达娃的歌声中,扎西不由想起曲珍,曲珍这会儿在做什么,她可曾想到我?
倒映在河水里的月亮晃晃悠悠,扎西看着一会儿碎掉,一会儿还原的月亮,曲珍的脸庞也在水中晃晃悠悠。
长长的辫子,红扑扑的脸,曲珍的眼睛中透着一股忧伤。
同一时间曲珍也坐在村边的一条小河旁……
看着水中的月亮,曲珍嘴里嘀咕着,这个扎西,怎么走的时候都不说一声呢。难道他一点都不想我。曲珍拿起小石子丢向水里的月亮。
水中的月亮被小石子砸碎了,银色的碎片在水中摇晃着。
难道连月亮都在幸灾乐祸?
曲珍连连拿起脚边的小石子丢进水里。眼泪也慢慢浸在眼眶中,泪花中也满是碎碎的月亮。
一个圆。两个圆。三个圆……
曲珍惊奇地发现,水中竟然晃着九个月亮,晃啊晃的。
难道是眼睛花了?她揉了揉眼睛,还是九个。
曲珍赶紧在心里默念着六字真言:“我不该对着神河说坏话的,原谅我。”
九个月亮在水面上晃啊晃,曲珍心里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清凉凉的,那九个月亮晃进了曲珍的眼睛,晃啊晃的,又晃进了曲珍的心里。
“曲珍见到九个月亮了。”
第二天,村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围到多吉老人的房前,但曲珍还是和以前一样安静,甚至更安静了。她慢慢地扫着院子,脸上多了一份安详。村里的人都想从曲珍的身上看出什么,可什么都没看到。
多吉老人也还是一样的沉默。“这对奇怪的父女。”本来以为多吉老人会针对曲珍见了九个月亮的事情说点什么的村里人,最终没得到满足,终于很不爽地走了。
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又跑了。和扎西一样。村里的老人在一起时,总忍不住提起扎西的名字,都是这个坏小子,在老人们的心里,年轻人都是被扎西带走的。村里的一些老人总很紧张地盯着年轻的小伙小姑娘们,生怕不小心又跑出去几个。
“造孽啊。不好好在家。”
走了的人们,到了外面过什么样的日子?村里的人从来不知道,因为从未见谁回来。
日子还是一样地过,太阳每天从山这边游荡到山那边,江水一遍遍拍打着大山。但村里多了一股紧张的气息。
在一个毫无预兆的黄昏,一场虫雨来到永格。那虫子忽然从天而降。铺天盖地,黑绿色指甲大的小虫子像倾盆大雨一样落在了永格村。
这个傍晚,村里只有多吉老人家的窗户是关上的,每一扇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十来分钟的虫雨一会儿就过去了,村里的小道都被黑绿的小虫子铺得满满的,当村里的人们在虫雨结束后正忙着打扫飘到房间里的小虫时,曲珍却不慌不忙、悠悠地打开自家的窗户,坐在宽大的窗栏上敲起手鼓,开始唱起了歌。
在村里人的记忆中,曲珍可不会唱歌,虽说藏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可曲珍什么都不会,天性呆滞,连朋友都没有。
曲珍的歌声很奇特,与其他人唱得高昂嘹亮的藏歌相比,她的歌声显得懒洋洋的,好像是无意间乱哼哼而已,可仔细听,那音乐却又带着一种缥缈的神奇韵味,曲珍那略带沙哑的音色让人听了只觉得心里很舒坦,在舒坦后心尖却被一小丝莫名的思绪轻轻地拉扯着。当曲珍敲起手鼓开始唱歌时,她那并不是很大的歌声及鼓声却能穿透村里的藏房、牛棚、柴房,传遍到村里的每个角落。
可这会儿,村里的人都为那从天而降的小虫子们忙得焦头烂额,曲珍的歌声也像无形的小虫子一样,悠悠地传入到村里的每个房子里,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村民们手慌脚乱地收拾着飘到灶台上的虫子、飘到酒碗的虫子、飘到水缸里的虫子、飘到被褥上的虫子,还被那钻进耳朵的曲珍那慵懒沙哑的歌声搞得有点晕头晕脑的。
村里的卓嘎感到无法忍耐,本来,正在打扫羊圈的她已经被乱叫的羊群搞得心烦意乱,老不小心踩上羊粪疙瘩,她直接从羊圈里的羊胸脯上揪了两团柔软的羊毛塞进耳朵,可曲珍的歌声和那不紧不慢的手鼓声还是穿过耳里的两团羊毛直达她的耳膜,化为无数只小虫子把她的心搞得直痒痒,卓嘎不知道怎么的,只感到脑子里被曲珍的声音绞得一团糟,肚子里怄了一肚子气,她使劲把耳朵里的羊毛团掏出来,把手里的扫帚直接往地上一丢,拿起一块石头冲到多吉老人的房前,对着坐在窗前的曲珍大声叫道:“唱什么唱。”
此时的曲珍完全没了往日的呆滞,脸上带着安详的淡淡的笑容,悠然自得地唱着自己的歌,夕阳照射下的曲珍全身散发着金光,那光芒反射进卓嘎的眼中,卓嘎看呆了,手中的石头到底没丢出去,她就一直站在楼下听着曲珍唱歌。
唱了会儿,曲珍没事一样跳下窗台,进了房间。卓嘎这个时候才慢慢回过神来,看看手中的石头,她连连吐着口水,把石头愤愤地砸向曲珍家的院子里。
“哎哟!砸到我了。”
“臭小子你给我下来。”
扎西气冲冲地站在树下骂着正在爬树的小男孩,那小男孩动作灵敏,已经飞快地爬到树上,坐在树枝茂密处,扎西一边骂着一边躲避着男孩碰落的核桃不落在自己的头上。
刚刚才和男孩的阿妈谈好,十元钱买下小男孩手中的小弓。可男孩的阿妈刚收到钱,扎西正要拿小弓时,小男孩却拿着小弓一溜烟跑到这个大树上去。
当扎西看到那小弓时,眼睛都亮了。多好的一把弓,做工讲究,上面还镶着松耳石,虽然已经凋落了几颗,但肯定能值钱的。
小男孩的阿妈很紧张地跟着站在一旁,她手里还握着扎西递给她的十元钱,她也正想把钱装进口袋里,还在盘算着,没想到一把小弓竟然把一年里的盐巴钱都找到了。可孩子就跑了。
扎西点了一支烟,他才不急呢。等着男孩的阿妈来叫吧,扎西看那女人看钱的眼神就知道今天他的生意又成功了。
她也加入了叫喊的行列,她的喊声果然更起效果:“再不下来,打断你的腿。”树上的小男孩极不情愿地爬了下来,并把小弓藏到身后,却被他的阿妈一把抢过来,放在扎西的手里。
“藏狼扎西。”凭借这一股狠劲以及康巴人特有的聪慧。好多道上的人这样称呼扎西,在生意场上多年,扎西跌倒后,又起来,又跌倒,又起来,如今的扎西已经很难再跌倒了。
靠着收集的好东西,扎西又赚了一笔。
他已经如鱼得水一般溶入这土黄色的小城,从外边看上去,扎西已经变为一个仪表堂堂的城市人。衣着光鲜,头发贼亮,怀里装着大把的钞票自由地出入各个饭店、歌舞厅。
如今的扎西和达娃早不喜爱看电影了。何况这年头,谁还看电影。想看就放录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多么惬意。
扎西从工地出来后,达娃也不在那里做了。扎西慢慢发达起来,达娃开了一家卡拉OK厅,每天生意还很好,扎西在空闲的时候,会到店里来帮忙。扎西走的地方多了,在他的帮助下,达娃的OK厅拥有小城里最好的音响和最前卫的音乐碟子。达娃还请了一个乡下女孩,平时她就悠闲地做老板,闲着收钱。 "
但这段时间,达娃有点闲不住了。
县城的歌舞团里分来几个艺校的漂亮妞,虽然都是藏族女孩,但那些女孩说话都软软的,从里到外,像奶油一样,这些女孩总会被人约来歌厅里玩。
同她们一起来的人各式各样的都有,老板,政府工作人员,街上的小混混,都是这些女孩的朋友。但女孩们总是一起来,一起走。达娃心里也希望这些女孩天天来。
快下雪了,扎西也停下手中的事情,他每年只需跑几趟,但每趟的行程都很远,一去就是几十天,甚至几个月。
这段时间,扎西就在达娃的店里帮着放音乐碟,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坐在吧台里,自己喝着啤酒,自己抽着烟,很安静。每当这个时候,达娃总感到一股满满当当的幸福,扎西越来越帅,和小城很多青年一样留着过肩的卷发,高高的鼻梁,紧闭的嘴唇像在思考着什么。
“老板,再来一件(一箱)啤酒。”又有人在叫酒了,达娃笑着赶紧过去,真好,客人高兴,难道这不是一个好年代吗?人人在唱歌,人人有酒喝。
达娃把酒送到那桌客人面前,把他们已经喝光的酒瓶收走,这几个是熟客了,在政府里工作的小青年。
“达娃姐姐,这是我的女朋友。”其中一位青年把一个女孩介绍给达娃。
“真漂亮,多好的姑娘,好福气。”达娃被这傻小子逗乐了。
唉,可能想对姑娘大胆表白,所以喝那么多酒。达娃大方地坐下来与他们喝了几杯酒,并说了不少祝福的话语。
吧台上,一位已经喝醉的女孩全身都趴到台上,说:“怎么找不到我想唱的歌。”扎西还是紧闭着嘴唇,眼皮都不抬一下,不紧不慢地翻看着歌碟。
“你会不会找?到底怎么找的?”喝醉的人好像都没好的耐性,那女孩对着扎西发脾气,扎西还是头都不抬,慢悠悠地翻看着歌碟。大概漂亮女孩的特性都一样,女孩被人宠坏了,和朋友在一起,谁不听她的?看扎西那么怠慢她,女孩自己心烦起来,对扎西说:“我自己来找。”
扎西把碟包放在吧台上,看都不看女孩,又坐下来,抽烟喝酒,一个人悠然自得,玩耍着一个鼻烟壶。
女孩的兴趣早已不在歌碟上,她歪着头研究着扎西。“和我聊天吧。”
“你朋友在那边,和他们聊吧。”扎西一直没看女孩。
“没意思啊,他们说的我都不感兴趣。”女孩一个人说着。她边说边用研究的眼光看着扎西。“你身上还真有艺术气质,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挑石头的。”扎西礼貌地回答。
“哈,开玩笑,但你肯定是最帅的石头工人。”
扎西被眼前的女孩逗乐了,这样的女孩,从小肯定长在蜜罐里,被身边的人宠着,长大了,因为漂亮,身边总有人围着对她好。
女孩叫琼,是歌舞团里跳舞的。再次来到OK厅时,女孩没喝酒,和朋友坐了会儿就到吧台找扎西。
扎西还是像往日一样,安静地喝着啤酒,抽着烟,放碟子。
“这么杂乱的环境,你怎么坐得住?”
“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大部分时候,都是琼一个人说着,扎西偶尔回答一下琼的问题。慢慢地,扎西和琼熟悉起来,扎西会给琼说一些他在途中遇到的人和事。
“我很孤独。”当琼一本正经地给扎西说着这样的话时,扎西忍不住笑了,扎西给琼说起他出去的事情,开着吉普车,有时走几天也不见一个村庄,偶尔还会遇到没有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只有你自己,那时,才知道孤独是什么。琼被扎西的旅途深深地吸引。
“我要和你一起去一次。”
扎西笑笑。怎么能给琼说出自己在做什么。收购文物?
“我要去采风,我要创作一个舞蹈,真正表现我们民族的舞蹈,你知道吗?我想让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根,都在我的舞蹈里得到呈现。但我却摸不到那东西,所以我很痛苦。”琼很认真地对扎西说。
达娃的紧张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她心里,扎西总该要和她结婚的,两人已经在一起七年了。像很多城里人一样,两人虽然没有领结婚证,可已经住在一起。每次,看着琼兴高采烈地和扎西聊天时,达娃的心里总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扎西好像已经好长时间没在她跟前这么开心地说过话了,两个人像左右手一样熟悉。
第一场雪来的时候,琼没有再来。达娃的心病也就解决了,她想,是不是该结婚了。
扎西的心里偶尔会想念一下琼,但想想也就过去,心里也没留下什么混迹,女孩肯定有很精彩的世界。
达娃二十五岁了。
达娃有事没事就在扎西面前开始数着自己的年龄,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扎西还不知道达娃的心计么,两人曾经有无数的争吵,可最后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了。达娃有个做生意的好头脑,这些年,她已经变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了。
“我们回家吧,回来就结婚。”
扎西也想,自己该回家一次了,出来那么久,从未回过家。
车路已经修到了离家几公里的地方,大山被这些路连了起来。
村里一切都没变。还是老样子。只是人少了好多,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了,只剩下年长的和年幼的才在村里。
几只山羊缩头缩脑地在路边穿行。
太阳还是一样刺眼地游荡在大山间。到了村口,扎西看到一群小孩围坐成一圈正开心地嬉笑着。见到扎西,都觉得很奇怪,有个年纪稍大一点的迟疑地喊了一声:“哥哥扎西?”
扎西笑了,离开的时间真长了,居然回村来,有人不认识他。
小孩们躲躲藏藏地拿着什么东西。扎西一看就明白了,小孩们在玩着情卦。他笑着离开了孩子们。
小伙子
房前屋后响着的是你的马铃声,
我心中明白你的愿望,
可盯着我的是父母明亮的双眼
我怎敢让你走进我的家门
你说黑母鸡下的也是白白的鸡蛋
我们的事情也要说个黑白分明
我俩就像白白的玉碗里盛上白白的奶汁
活着是白白的良心
死了是白白的骨头
(白白的骨头,藏族表白自己的真诚良心,意思为像石头一样洁白无瑕)
那次是唯一的一次,曲珍也加入到伙伴的行列中,大家很开心地玩。参加情卦的人,都拿出一件最能代表自己心思的小物件放在一人手中。掌管物件的人将所有的小物件在手里摇晃后,暗中取出一件,让大家猜。于是其它人便猜测物件属谁所有,并针对物主爱情上的处境唱出一串有趣的情歌。
[FS:PAGE] 这个时候,天才刚开始透亮,太阳还没出来,藏在半山腰的永格村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村里的人都还没起床,那一声声鸡鸣在雾中清晰地响亮着。
临走之前,扎西环视自己居住了二十年的老屋,屋子因为年久失修,像一个衰老的老人立在那里,全身发出衰败之气。“终于要离开这里了。”扎西已经被这股衰败之气熏得头晕眼花,他讨厌这个地方,虽然他就在这里出生,可他还是讨厌这个地方,讨厌这里成天臭烘烘的牛粪味,讨厌这里随处可踩到的羊屎疙瘩,讨厌这里有那么多传说,而这里的人除了沉湎于曾有的传说中的辉煌天天喝酒,就不想想能干点其它的什么。
扎西的父母去拉萨朝拜了,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可一点消息都还没有。
这个早晨扎西可不想遇到什么人。永格有个奇怪的习俗,除了去圣地拉萨朝拜,谁也不能想什么理由来离开这个村子,因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知道了,总会出来阻挠,如果阻挠不成功,则通过其它多种渠道来施加压力。扎西从记事开始就发现村里没一个离开的。而那些去朝拜圣地的人,总会面黄肌瘦地回到村里,回到村里的人从不讨论朝圣途中遇到的事情,也不讨论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日子依然和从前一样。只是一些男人在酒醉后开始吟唱“古老的八角街上,窗户比门还多,窗户里的姑娘们,骨头比肉还软”。
想到这首歌,扎西的心里就有个东西在骚动不安,他一直不理解这首歌到底唱的是什么,但总觉得这歌词给人无限的向往。
“会见到的。还有很多没见过的东西也会看到的。”扎西真忍不住要把这句话喊出来,可他不敢,这会儿,他不想别人看到他,这感觉真让人激动而又压抑。
扎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清晨的雾气,觉得心里有个东西快要奔突出来。而脚上也像长了翅膀,要飞起来一样。
“哎哟!”扎西的大脚趾碰在一块尖石上,扎西忍不住张开嘴吸着丝丝的冷气,他弯下腰去用手捂住脚,看到自己那双已经破烂不堪的黄胶鞋此时开了个大口子,而那块撞到脚的石块,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经文。“又是那个臭老头干的。”扎西说的臭老头是曲珍的爸爸——多吉老人。
多吉老人是个会飞的人。从小扎西就听别人这么说,可谁也没见过多吉老人飞起来过。这个老人平时沉默寡言,一有时间就拿着石板刻藏经,或者东挖挖,西挖挖。总有些“宝贝”被他挖出来,那些宝贝,不外乎是些写着经文的石块,村里的老人说,是他事先藏好了哄人的。
多吉老人一人带着女儿曲珍,曲珍也像老人一样沉默寡言。
多吉老人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头一个高高的小山包上,俯视着永格这个小山村,只要是在村里,任何一家都能看到多吉老人的房子。多吉老人平时也不多和村里的人来往,像他的房子一样,高傲而又孤独地存在于村民的记忆中。永格总的也就有二十多户人家,七零八落的房子架在山腰的一个小山洼中。
扎西什么都没带,未来总是美好的,干嘛还要带上一些破东西呢。扎西的家里,每一件东西他熟悉得闭上眼睛都不会拿错,而且也没什么能让他带走的东西。
想到村里的老人发现他出走,想到父母回到家找不到他时的表情,扎西心里不由一阵阵兴奋。这群老家伙,一个个呆如木鸡,肯定只能吹胡子。
村里唯一让扎西放不下的人还是曲珍。想到时常喜欢沉默,一整天都没有一句话,那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从不正眼看别人的曲珍,扎西那躁动不安的心一下下被说不清楚的缕缕思绪勾住。
“不知道曲珍知道我走了,会怎么想。”扎西不由这么想,“当我有了好日子过,我就回来找曲珍。”这么一想,扎西就觉得对曲珍有交代了。
“曲珍,你等着我过好了,就回来了。”
脚上大拇指丝丝地扯着心口疼,扎西一瘸一瘸地走着。怎么刚出门就遇到这样的事。他不由连连吐口水。“我应该像羚羊过山冈一样走出村子才对。”扎西不由在心里嘀咕着。都怪这个老头,难道说他有什么法术?等会儿经过他的房子时,一定要对着他的房子吐口水,才能去晦气。
酝集着一泡口水,扎西快到多吉老人的房前了。
刚要把那积攒了好一会儿的口水吐在多吉老人房子的墙根脚,扎西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多吉老人和女儿曲珍正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一位身着艳丽服装的女人,女人身上还背着一个热巴鼓,腰间拴着金色丝带,脚上还戴着铃铛。
曲珍怎么那么小了,好像才十岁的样子,被多吉老人牵着手站在门口。扎西的一泡口水硬是没吐出来。这个女人好像是曲珍的母亲,怎么会在这里,曲珍怎么变小了。扎西还记得小时候见过的曲珍的母亲——她丝毫没有女主人的味道,却像一个客人,什么都不做,经常坐在火塘边哼着歌,还喝酒。村里从来没有女人像这样的。喝酒后的曲珍的母亲坐在火塘边还是哼着歌,她的那些歌,从来没有人能听懂。
但这会儿,戴上脚铃和系着金丝腰带的女人却全身都散发着一股光彩,多吉老人和他那房子被这光彩照出腐朽的气息。他们三个人谁都没发现旁边的扎西。
曲珍的母亲整理过背上的热巴鼓后,就转身大踏步向前走。多吉老人站在后面大声地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明年回就明年回,想后年回就后年回。”踏着脚铃声,曲珍的母亲越走越远。
曲珍只是张着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还是谁都没看到扎西,扎西好像隔着一个东西看着这一切。
“我也要赶紧走。”他追向曲珍的母亲,只听到铃铛声越来越远,山路上只是扎西一个人。
永格离扎西也越来越远,被扎西远远地抛在身后。
太阳慢慢出来,在光秃秃的大山间游荡,大山一座连着一座,山底下的那条江依然静静地流淌,没有一点点绿色的大山看上去一片死寂,只有游荡的太阳发出刺眼的光芒。
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扎西已经晕头晕脑。从早上出来到现在,他没吃过一点东西,浑身上下,像他的肚子一样空空荡荡。扎西甩着两只手奋力走着,风在他的脚下软软地飘……
终于,看见公路了。
看着向远方延伸的公路,扎西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未来,在远方吗?未来,想到这个词,扎西觉得像他此时的肚子一样,更加空空荡荡。
“拖,拖,拖……”一辆拖拉机远远过来了。
一群男女兴高采烈地坐在上面。
“年轻人,要去哪里?”车上有人问扎西了。
“我……”
车上戴着红头帕的女人们笑开了。
扎西清了清嗓子,用手指着远方,大声地对车上的人喊到:“我要去那边。
“年轻人,上车吧。”车上的人热情地叫着扎西。
扎西歪着头想想,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便跳上了拖拉机的车厢。
“挤到我了。”“过去一点。”扎西才发现,车厢很拥挤。他想缩到一个地方,却又踩到另一个人的脚。
“稳住了,出发了。”开车的人吆喝着。
“拖……拖……拖……”拖拉机发动了,车厢里站的人又开始嚷嚷起来。一股汗臭和灰尘味很刺鼻地包围着扎西。他看着车子在路上扬起的灰,暗暗在心里说着:“再见,永格。”
还没来得及伤感,车上有个人起头唱起了歌,一车人都跟着唱起来。“呵,藏歌都是一样的。”这些人扎西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唱的藏歌扎西可是熟悉得很。刚刚在扎西心里泛起的伤感立马被歌声挤跑了。
“过来这边一点。”一个戴红头帕的女孩轻轻拉着扎西的衣角说,扎西靠着她站了过去,这是个好位置,能扶到车厢的边上,一下稳住了。扎西对这个女孩感激地笑了笑。女孩却把脸别过去了,只把一个红头帕留在扎西的眼前。
一路上,扎西慢慢和同车的人熟悉了。原来大家一样,都是住在藏在大山中的村子里。路上休息时,那个带红头帕的女孩还把带着的糌粑给扎西吃。在交谈中扎西知道了女孩叫达娃。
“你为什么要出来呢?”扎西问达娃。
达娃抓了抓头,想了半天才说:“我也不知道,人人都在走,都说外面好,我就来了。”由于达娃给扎西让位子,还把东西分给扎西吃,无形中,扎西和达娃慢慢熟悉起来。
黄昏的时候,拖拉机到城里了。太阳的余晖中,一个土黄色的小城就在那里。本来兴高采烈的一车人现在却一个都不说话了。大家都瞪着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
“拉萨?”扎西忍不住问。
司机“呸”了一声,说:“这是县城。拉萨离这里还有好几千公里呢。”
几千公里,听到这个距离。有人伸了伸舌头。
街上不是很热闹,有几头牦牛悠闲地逛在路中央,被它们挡住的车一声接一声的喇叭响起来,它们才甩甩尾巴慢腾腾地走开。
拖拉机带着一车人驶进城里。在一个施工地点停住了,全车的人都跳下来。
扎西这个时候才觉得身子快散架了。师傅过来收钱了。扎西什么都没有。达娃大概已经知道了扎西肯定没钱,帮扎西付过车钱,问:“你要去什么地方?”扎西摇着头,说:“不知道。”
这个时候,师傅大声说话了:“大家没地方去的,可以去这里做活。”他指着正在盖建的大楼说。
达娃望了望扎西,好像是在问扎西去不去。
扎西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两个人笑了笑,一群人又跟着师傅走。果然,有地方可以住,还有吃的东西了。
达娃在工地里负责做饭,而扎西,要跟着好多工人一起挑石头水泥。
扎西就这样在这个土黄色的小城安顿下来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扎西和达娃一直在工地上做活。一个地方的工程做完了,他们跟着别人又搬到另一个地方开始。一栋栋新房子建了起来,扎西每看到这些新房子时,心里就有了一点念头,我在为这个城市建设呢。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自豪感。
一天,达娃约扎西去看电影。
收工后,两人换了干净衣服来到电影院。心里想:我们也是城市人了。
电影院前,两人相互笑望着对方。扎西还特意买了两碗炒葵瓜子把口袋装得满满的。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瓜子,这就是城市人的生活。扎西心里高兴坏了,自己怎么这么聪明。
扎西和达娃已经来看过好几次电影了。虽然电影票有点贵,但两个人几个月就会来一次,电影里那么多稀奇的东西。多好看啊。
这一天放的是一部功夫片,李连杰在里面出神的武功让扎西看得惊叹不已,当李连杰被别人打败时,扎西跟着沮丧,当李连杰又打赢别人时,扎西跟着连连叫好。
“乡巴佬别叫了。”终于旁边有人叫出比扎西的嗓门更大的声音,扎西不知道是对着他喊的,仍然跟着电影中的情节发展大叫着。“真过瘾!”他还得意地看了看达娃。
却不想达娃拉了拉他的衣服说:“别叫了,人家都在说你了。”
“我?”扎西奇怪了。“看电影就应该这样看嘛,我们村里谁家结婚时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时不就这样吗?”
“乡巴佬,再叫把你赶出去。”这时,查票的过来了。
电影里的场面依然很精彩,但扎西怎么看都觉得不是滋味了。达娃也感觉到扎西的不适,对他耸耸肩说:“管他们呢,自己看自己的。”
还没等到电影结束,扎西就把达娃拉出了电影院。电影院斜对面的歌舞厅正热火朝天地响着舞曲,几个从里面出来的漂亮姑娘很不屑地从扎西和达娃身边走过,留下一股刺鼻的香粉味。
“你说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人么?”扎西忍不住问达娃。
“我们生活在这里啊。”达娃很疑惑地看着扎西。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底算是哪里的人?”扎西忽然感觉有些说不清楚的东西。
达娃不知道怎么接口,便像城里人一样挽着扎西的胳膊,说:“我们回去吧。”
电影院里还传出打斗的声音,月亮亮晃晃地挂在天上,扎西看着地上的影子,忽然一种茫然占据他的心,空捞捞的。
这个晚上,扎西失眠了。他想起以前在村子里时,碰到谁家结婚时,或者村里人聚在一起,总是大声地笑,大声地说,多么快乐。
一连好几天,他都没去找达娃。默默地在工地做着自己的活,达娃感觉到扎西的异样了。她知道扎西肯定还在为那个晚上被别人说了而在生气。
吃过晚饭,她把自己的脸洗得干干净净,还偷偷抹上一点同伴的雪花膏,去找扎西。
果然,扎西一个人在宿舍里。几十人打通铺睡的宿舍里,什么味道都有,又脏又乱,达娃捂着鼻子坐到扎西旁边。
扎西看了看达娃,没说话。
达娃拉扯着扎西:“出去逛逛。”
扎西极不情愿地跟着达娃出了工地的宿舍,路上遇到几个工友挤眉弄眼地对着他们嚷嚷。达娃却是大大方方地拉着扎西的手。
一路上,扎西一直没说话。
达娃可不喜欢这样沉默的气氛,她在心里暗暗懊悔着那雪花膏是不是白用了,怎么扎西一眼都不看她。
两人慢慢走到那池河边,河水无声地慢慢流着。扎西和达娃坐在河边的草地上。“我这几天总在想,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我要到哪儿去,我该做什么?”
达娃听着扎西说的话,忽然感到很陌生:“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有吃的,有住的,我们的工钱还不少呢,我们已经在城里生活了。慢慢地,我们会变成城里人的。”达娃越说越开心。
“我这几天特别想家,出来以后,从未这么想过。”扎西低着头闷闷地说。
“谁都会想家的。哎,我给你唱歌吧。”达娃的声音很好听,甜甜的,脆脆的。“高高的雪山像弯弯的神弓,下山的牦牛像飞射的神箭……”
在达娃的歌声中,扎西不由想起曲珍,曲珍这会儿在做什么,她可曾想到我?
倒映在河水里的月亮晃晃悠悠,扎西看着一会儿碎掉,一会儿还原的月亮,曲珍的脸庞也在水中晃晃悠悠。
长长的辫子,红扑扑的脸,曲珍的眼睛中透着一股忧伤。
同一时间曲珍也坐在村边的一条小河旁……
看着水中的月亮,曲珍嘴里嘀咕着,这个扎西,怎么走的时候都不说一声呢。难道他一点都不想我。曲珍拿起小石子丢向水里的月亮。
水中的月亮被小石子砸碎了,银色的碎片在水中摇晃着。
难道连月亮都在幸灾乐祸?
曲珍连连拿起脚边的小石子丢进水里。眼泪也慢慢浸在眼眶中,泪花中也满是碎碎的月亮。
一个圆。两个圆。三个圆……
曲珍惊奇地发现,水中竟然晃着九个月亮,晃啊晃的。
难道是眼睛花了?她揉了揉眼睛,还是九个。
曲珍赶紧在心里默念着六字真言:“我不该对着神河说坏话的,原谅我。”
九个月亮在水面上晃啊晃,曲珍心里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清凉凉的,那九个月亮晃进了曲珍的眼睛,晃啊晃的,又晃进了曲珍的心里。
“曲珍见到九个月亮了。”
第二天,村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围到多吉老人的房前,但曲珍还是和以前一样安静,甚至更安静了。她慢慢地扫着院子,脸上多了一份安详。村里的人都想从曲珍的身上看出什么,可什么都没看到。
多吉老人也还是一样的沉默。“这对奇怪的父女。”本来以为多吉老人会针对曲珍见了九个月亮的事情说点什么的村里人,最终没得到满足,终于很不爽地走了。
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又跑了。和扎西一样。村里的老人在一起时,总忍不住提起扎西的名字,都是这个坏小子,在老人们的心里,年轻人都是被扎西带走的。村里的一些老人总很紧张地盯着年轻的小伙小姑娘们,生怕不小心又跑出去几个。
“造孽啊。不好好在家。”
走了的人们,到了外面过什么样的日子?村里的人从来不知道,因为从未见谁回来。
日子还是一样地过,太阳每天从山这边游荡到山那边,江水一遍遍拍打着大山。但村里多了一股紧张的气息。
在一个毫无预兆的黄昏,一场虫雨来到永格。那虫子忽然从天而降。铺天盖地,黑绿色指甲大的小虫子像倾盆大雨一样落在了永格村。
这个傍晚,村里只有多吉老人家的窗户是关上的,每一扇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十来分钟的虫雨一会儿就过去了,村里的小道都被黑绿的小虫子铺得满满的,当村里的人们在虫雨结束后正忙着打扫飘到房间里的小虫时,曲珍却不慌不忙、悠悠地打开自家的窗户,坐在宽大的窗栏上敲起手鼓,开始唱起了歌。
在村里人的记忆中,曲珍可不会唱歌,虽说藏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可曲珍什么都不会,天性呆滞,连朋友都没有。
曲珍的歌声很奇特,与其他人唱得高昂嘹亮的藏歌相比,她的歌声显得懒洋洋的,好像是无意间乱哼哼而已,可仔细听,那音乐却又带着一种缥缈的神奇韵味,曲珍那略带沙哑的音色让人听了只觉得心里很舒坦,在舒坦后心尖却被一小丝莫名的思绪轻轻地拉扯着。当曲珍敲起手鼓开始唱歌时,她那并不是很大的歌声及鼓声却能穿透村里的藏房、牛棚、柴房,传遍到村里的每个角落。
可这会儿,村里的人都为那从天而降的小虫子们忙得焦头烂额,曲珍的歌声也像无形的小虫子一样,悠悠地传入到村里的每个房子里,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村民们手慌脚乱地收拾着飘到灶台上的虫子、飘到酒碗的虫子、飘到水缸里的虫子、飘到被褥上的虫子,还被那钻进耳朵的曲珍那慵懒沙哑的歌声搞得有点晕头晕脑的。
村里的卓嘎感到无法忍耐,本来,正在打扫羊圈的她已经被乱叫的羊群搞得心烦意乱,老不小心踩上羊粪疙瘩,她直接从羊圈里的羊胸脯上揪了两团柔软的羊毛塞进耳朵,可曲珍的歌声和那不紧不慢的手鼓声还是穿过耳里的两团羊毛直达她的耳膜,化为无数只小虫子把她的心搞得直痒痒,卓嘎不知道怎么的,只感到脑子里被曲珍的声音绞得一团糟,肚子里怄了一肚子气,她使劲把耳朵里的羊毛团掏出来,把手里的扫帚直接往地上一丢,拿起一块石头冲到多吉老人的房前,对着坐在窗前的曲珍大声叫道:“唱什么唱。”
此时的曲珍完全没了往日的呆滞,脸上带着安详的淡淡的笑容,悠然自得地唱着自己的歌,夕阳照射下的曲珍全身散发着金光,那光芒反射进卓嘎的眼中,卓嘎看呆了,手中的石头到底没丢出去,她就一直站在楼下听着曲珍唱歌。
唱了会儿,曲珍没事一样跳下窗台,进了房间。卓嘎这个时候才慢慢回过神来,看看手中的石头,她连连吐着口水,把石头愤愤地砸向曲珍家的院子里。
“哎哟!砸到我了。”
“臭小子你给我下来。”
扎西气冲冲地站在树下骂着正在爬树的小男孩,那小男孩动作灵敏,已经飞快地爬到树上,坐在树枝茂密处,扎西一边骂着一边躲避着男孩碰落的核桃不落在自己的头上。
刚刚才和男孩的阿妈谈好,十元钱买下小男孩手中的小弓。可男孩的阿妈刚收到钱,扎西正要拿小弓时,小男孩却拿着小弓一溜烟跑到这个大树上去。
当扎西看到那小弓时,眼睛都亮了。多好的一把弓,做工讲究,上面还镶着松耳石,虽然已经凋落了几颗,但肯定能值钱的。
小男孩的阿妈很紧张地跟着站在一旁,她手里还握着扎西递给她的十元钱,她也正想把钱装进口袋里,还在盘算着,没想到一把小弓竟然把一年里的盐巴钱都找到了。可孩子就跑了。
扎西点了一支烟,他才不急呢。等着男孩的阿妈来叫吧,扎西看那女人看钱的眼神就知道今天他的生意又成功了。
她也加入了叫喊的行列,她的喊声果然更起效果:“再不下来,打断你的腿。”树上的小男孩极不情愿地爬了下来,并把小弓藏到身后,却被他的阿妈一把抢过来,放在扎西的手里。
“藏狼扎西。”凭借这一股狠劲以及康巴人特有的聪慧。好多道上的人这样称呼扎西,在生意场上多年,扎西跌倒后,又起来,又跌倒,又起来,如今的扎西已经很难再跌倒了。
靠着收集的好东西,扎西又赚了一笔。
他已经如鱼得水一般溶入这土黄色的小城,从外边看上去,扎西已经变为一个仪表堂堂的城市人。衣着光鲜,头发贼亮,怀里装着大把的钞票自由地出入各个饭店、歌舞厅。
如今的扎西和达娃早不喜爱看电影了。何况这年头,谁还看电影。想看就放录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多么惬意。
扎西从工地出来后,达娃也不在那里做了。扎西慢慢发达起来,达娃开了一家卡拉OK厅,每天生意还很好,扎西在空闲的时候,会到店里来帮忙。扎西走的地方多了,在他的帮助下,达娃的OK厅拥有小城里最好的音响和最前卫的音乐碟子。达娃还请了一个乡下女孩,平时她就悠闲地做老板,闲着收钱。 "
但这段时间,达娃有点闲不住了。
县城的歌舞团里分来几个艺校的漂亮妞,虽然都是藏族女孩,但那些女孩说话都软软的,从里到外,像奶油一样,这些女孩总会被人约来歌厅里玩。
同她们一起来的人各式各样的都有,老板,政府工作人员,街上的小混混,都是这些女孩的朋友。但女孩们总是一起来,一起走。达娃心里也希望这些女孩天天来。
快下雪了,扎西也停下手中的事情,他每年只需跑几趟,但每趟的行程都很远,一去就是几十天,甚至几个月。
这段时间,扎西就在达娃的店里帮着放音乐碟,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坐在吧台里,自己喝着啤酒,自己抽着烟,很安静。每当这个时候,达娃总感到一股满满当当的幸福,扎西越来越帅,和小城很多青年一样留着过肩的卷发,高高的鼻梁,紧闭的嘴唇像在思考着什么。
“老板,再来一件(一箱)啤酒。”又有人在叫酒了,达娃笑着赶紧过去,真好,客人高兴,难道这不是一个好年代吗?人人在唱歌,人人有酒喝。
达娃把酒送到那桌客人面前,把他们已经喝光的酒瓶收走,这几个是熟客了,在政府里工作的小青年。
“达娃姐姐,这是我的女朋友。”其中一位青年把一个女孩介绍给达娃。
“真漂亮,多好的姑娘,好福气。”达娃被这傻小子逗乐了。
唉,可能想对姑娘大胆表白,所以喝那么多酒。达娃大方地坐下来与他们喝了几杯酒,并说了不少祝福的话语。
吧台上,一位已经喝醉的女孩全身都趴到台上,说:“怎么找不到我想唱的歌。”扎西还是紧闭着嘴唇,眼皮都不抬一下,不紧不慢地翻看着歌碟。
“你会不会找?到底怎么找的?”喝醉的人好像都没好的耐性,那女孩对着扎西发脾气,扎西还是头都不抬,慢悠悠地翻看着歌碟。大概漂亮女孩的特性都一样,女孩被人宠坏了,和朋友在一起,谁不听她的?看扎西那么怠慢她,女孩自己心烦起来,对扎西说:“我自己来找。”
扎西把碟包放在吧台上,看都不看女孩,又坐下来,抽烟喝酒,一个人悠然自得,玩耍着一个鼻烟壶。
女孩的兴趣早已不在歌碟上,她歪着头研究着扎西。“和我聊天吧。”
“你朋友在那边,和他们聊吧。”扎西一直没看女孩。
“没意思啊,他们说的我都不感兴趣。”女孩一个人说着。她边说边用研究的眼光看着扎西。“你身上还真有艺术气质,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挑石头的。”扎西礼貌地回答。
“哈,开玩笑,但你肯定是最帅的石头工人。”
扎西被眼前的女孩逗乐了,这样的女孩,从小肯定长在蜜罐里,被身边的人宠着,长大了,因为漂亮,身边总有人围着对她好。
女孩叫琼,是歌舞团里跳舞的。再次来到OK厅时,女孩没喝酒,和朋友坐了会儿就到吧台找扎西。
扎西还是像往日一样,安静地喝着啤酒,抽着烟,放碟子。
“这么杂乱的环境,你怎么坐得住?”
“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大部分时候,都是琼一个人说着,扎西偶尔回答一下琼的问题。慢慢地,扎西和琼熟悉起来,扎西会给琼说一些他在途中遇到的人和事。
“我很孤独。”当琼一本正经地给扎西说着这样的话时,扎西忍不住笑了,扎西给琼说起他出去的事情,开着吉普车,有时走几天也不见一个村庄,偶尔还会遇到没有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只有你自己,那时,才知道孤独是什么。琼被扎西的旅途深深地吸引。
“我要和你一起去一次。”
扎西笑笑。怎么能给琼说出自己在做什么。收购文物?
“我要去采风,我要创作一个舞蹈,真正表现我们民族的舞蹈,你知道吗?我想让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根,都在我的舞蹈里得到呈现。但我却摸不到那东西,所以我很痛苦。”琼很认真地对扎西说。
达娃的紧张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她心里,扎西总该要和她结婚的,两人已经在一起七年了。像很多城里人一样,两人虽然没有领结婚证,可已经住在一起。每次,看着琼兴高采烈地和扎西聊天时,达娃的心里总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扎西好像已经好长时间没在她跟前这么开心地说过话了,两个人像左右手一样熟悉。
第一场雪来的时候,琼没有再来。达娃的心病也就解决了,她想,是不是该结婚了。
扎西的心里偶尔会想念一下琼,但想想也就过去,心里也没留下什么混迹,女孩肯定有很精彩的世界。
达娃二十五岁了。
达娃有事没事就在扎西面前开始数着自己的年龄,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扎西还不知道达娃的心计么,两人曾经有无数的争吵,可最后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了。达娃有个做生意的好头脑,这些年,她已经变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了。
“我们回家吧,回来就结婚。”
扎西也想,自己该回家一次了,出来那么久,从未回过家。
车路已经修到了离家几公里的地方,大山被这些路连了起来。
村里一切都没变。还是老样子。只是人少了好多,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了,只剩下年长的和年幼的才在村里。
几只山羊缩头缩脑地在路边穿行。
太阳还是一样刺眼地游荡在大山间。到了村口,扎西看到一群小孩围坐成一圈正开心地嬉笑着。见到扎西,都觉得很奇怪,有个年纪稍大一点的迟疑地喊了一声:“哥哥扎西?”
扎西笑了,离开的时间真长了,居然回村来,有人不认识他。
小孩们躲躲藏藏地拿着什么东西。扎西一看就明白了,小孩们在玩着情卦。他笑着离开了孩子们。
小伙子
房前屋后响着的是你的马铃声,
我心中明白你的愿望,
可盯着我的是父母明亮的双眼
我怎敢让你走进我的家门
你说黑母鸡下的也是白白的鸡蛋
我们的事情也要说个黑白分明
我俩就像白白的玉碗里盛上白白的奶汁
活着是白白的良心
死了是白白的骨头
(白白的骨头,藏族表白自己的真诚良心,意思为像石头一样洁白无瑕)
那次是唯一的一次,曲珍也加入到伙伴的行列中,大家很开心地玩。参加情卦的人,都拿出一件最能代表自己心思的小物件放在一人手中。掌管物件的人将所有的小物件在手里摇晃后,暗中取出一件,让大家猜。于是其它人便猜测物件属谁所有,并针对物主爱情上的处境唱出一串有趣的情歌。
有人唱起了这首歌,全部人合唱起来。大家都被歌中的氛围所感染,爱情,对孩子来说,什么也不懂,但大家都被那歌感动了,唱的人自己感动,听的人也感动,跟着一起唱。歌唱完了,大伙谁也没笑,都在暗暗想着谁的心里怀着这么深的感情。
当掌物人摊开手心,大家看到了,曲珍佩带着的绿松石展现在大家面前。
“曲珍。”
“啊。”
曲珍一把抢过自己的绿松石,就跑开了。
孩子们已经站了起来,围着扎西一起进了村子,扎西的行李也都被孩子们分担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和扎西不停地说着话。
扎西年迈的父母见到扎西,一点也不惊奇,他们好像已经早就料到这一天。
回到村里好多天了,扎西一直没见到曲珍。扎西的耳边可没少听别人说起曲珍的种种事情,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曲珍的歌声。
多吉老人还是不停地在石板上刻着东西。
要离开的头一个晚上,扎西听到曲珍坐在窗台上唱歌了。他赶紧跑到曲珍家楼下。
曲珍不看他,自己唱着歌。
听着曲珍的歌曲,扎西心里被什么东西撕扯着,全身上下都不自在,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感受了。“曲珍,别唱了。”
月光下,曲珍自己唱着,扎西在曲珍的歌声中好像看到一个远古的世界,大块块的石头,连绵不绝的海水,隆起的山脉。扎西走进了一个时间走廊。
扎西抱起自己的头。
最后一声鼓点停了下来,扎西的心也跟着舒坦了。
“干嘛,见我满脸都是皱皱,这么难受啊。”
曲珍变了,变调皮了。
“嗯,不是,嗯,是……”扎西结结巴巴的,他还在为刚才歌声中的世界所迷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曲珍跳下了窗台,站到扎西面前。用手比画了一下扎西的个子,继续说着:“我都有你高了哦。”
“嘿嘿。”
“长大了做我的媳妇。”
“你太讨厌了。”
“哼,你像只小鸟,赶紧长大,不然不要你了。”
“才不想理你。”
“你脸上怎么黑黑的,唉,是一牛屎啊。”
“呜……”
从小扎西就这么逗曲珍。现在却是扎西不知道说什么。回村里来,他最想见的就是曲珍。
“城里的日子怎么样?”
“很好啊。”
“怎么个好?”
“好多好东西呢。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城里的月亮比这个的亮么?”
“亮啊,又大又亮。”扎西话才说话,就被曲珍的鼓重重地敲在了头上。
“看你,吃的糌粑都还没拉干净,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了。”
“呵。”
时间从未向前走,也未曾过去,两个人笑着望着对方。
曲珍的眼睛转了转。又问:“那,那城里的姑娘漂亮么。”
“丑啊,都没你漂亮。”
曲珍开心地笑了起来。
“曲珍,你想过出去么?”
“为什么要出去?”
“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你干嘛还留在这里?”
“干嘛留在这里?”
“嗯。”
“这里有什么不好?”
曲珍纯真的话语带着小孩子的狡黠,让扎西回答不出来,感觉这么多年的好口才真是白用了。
“我阿爸让我好好唱歌,他说我在唱一个秘密。”
一阵咳嗽声从屋子里传出来,曲珍对着扎西吐了吐舌头。
“我要进去了。”曲珍转身就进了家门。
扎西还是像以前一样怕多吉老人,多吉老人见到扎西一句话都不说,头一扭就转开了,像村里的好多老人一样,扎西不明白,他怎么就把村里的老人全都得罪了。他带回来的礼物也被老人们拒绝了。
“老家伙。”扎西在心里不无恶意地暗暗称呼这些老人。
村里一些人家有了电视,那是在外打工的青年给家里买来的。
扎西也给家里买了电视,录像机,还有接受信号的天锅,可他发现父母根本不想多看那些玩意。
“哦,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才好。总不能和菩萨放在一起吧。”
试着放了几天的电视,就这么被放置到柴房里。
永格村是一个最蔑视现代化的村庄,外来的洋东西在这里都成了垃圾或者比垃圾还没用的东西。
反正每家的房子都很大,房子里放不下,放在院子里也行。
在外面那么一些年,扎西总在梦中回到村里,可现在他在村里却找不到位置。父母什么农活也不让他做,他天天就在村里东逛逛,西逛逛。
“曲珍长大了,曲珍已经二十二岁了。”
扎西的父母不停地在他耳边说着这个话,扎西怎么能不明白父母的意思呢。
“给你的。”
“这是什么?”
扎西摆弄着手里的录音机:“你说两句话。”
曲珍歪着头看着。“哩哩啦啦……哩哩啦啦。”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录音机里沙沙地重复着刚才曲珍发出的声音。
“啊,什么东西,在学我吗?”
“这是录音机。”
“录音机?”
“对,比如你唱什么,就可以录下来。很好玩吧。”
曲珍拿起录音机翻来覆去地看着,想看出点什么名堂。
“记录什么呢?”
“比如你的歌声。”
“歌声?”
“对。你不是说你在唱一个秘密吗,把它记录下来。”
“我不要。我的歌声在我心里呢,跑不掉。”曲珍把录音机还给扎西。想了想,她又拿起录音机来。“真能录下来吗?”
扎西点着头。曲珍说了一声,你等等我,就走开了。 "
过了一会儿,曲珍又来了。她拿起手鼓,换上平时节日里才穿的华贵的盛装。扎西想不明白曲珍要做什么。“把我的歌声录下来,留在你身边。放在怀里。”
曲珍开始唱歌了。扎西又看到那片大海,那崛起的山脉。他的脸跟着歌声变得龇牙咧嘴。曲珍用鼓棒重重地敲着扎西的头说:“看看你的表情。我怎么唱得下去。”
扎西好不容易调整一个笑容出来:“这样行吧。”
“哼,比哭还难看,真应该拿泡牛屎糊到你的脸上。”顺着曲珍的话,扎西深深地呼吸了口气,双手在脸上一抹:“糊上了。现在你可以唱歌了。”
从星星开始,到六字真言,到五姓诸佛,到神山,到万伞太阳,到纳福……曲珍唱得昏天黑地。从黄昏唱到天黑,从天黑唱到天亮,鼓点也一直响起。直到唱完,曲珍像生病一样脸色苍白,扎西也听得脸色苍白。
曲珍是仙女。扎西心里蹦出这个念头。
扎西再不敢起带曲珍离开这里的念头了。但他已经在村里留不住了。
旅游的热潮悄悄靠近了小城,OK厅的生意也越来越糟糕。
各类咖啡厅、酒吧、西餐馆在街上多起来。达娃坐不住了,她已经敏感地嗅到隐藏在小城里的种种气息,那股气息在召唤着她。
分析种种利弊后,达娃做了决定,搞餐饮文化。买地,起房子,装修,还是达娃一贯的风格,风风火火。扎西根本不用插手,但花的大部分都是他的积蓄,他心里不免有些心疼。
“达娃,你要折腾什么。”
“人就是要不断地向前走。还记得我们刚到这里时么,如果不是你先折腾,也许我们还在工地呢,所以折腾是好事。
“可是我累了。我不想做那么多事情。”
“不用你做,你闲着吧。我来折腾。”
从村里回城后,扎西一次都没出门。他感到自己生病了。
也正像达娃所说的一样,她根本不需要扎西来帮忙,在城里这么多年,因为后来的OK厅,达娃认识了很多的人,单位上的,社会上混的,做生意的,而且都关系不赖。
很快,房子起好了。
标准的藏式房,高高的三层,大大的院子,本来在二楼的厨房搬到院子里,围墙上一圈都放上了太阳伞,可以喝茶,一楼是餐厅,二楼是客房,三楼还是客房。
达娃的眼光果然不错。开张以来,生意一直不错。一批接一批的客人。每天都是满满的。达娃更忙了。扎西没什么事情可做,每天看碟子,喝酒。
“城里的人生活是怎么样的。”
“都一样的,但他们不做活。”
“不做活,那靠什么吃饭。”
“或者是做活的吧,反正不用种田,也不用放羊。”
“城里的人唱歌吗?”
“嗯,城里的人可喜欢唱歌了,还喜欢喝酒。”
“那不是和我们这里一样嘛。”
“也不一样,比如结婚时,我们唱的歌他们也唱,但好像很短很短。”
“很短很短?”
“比如我们祈福的三天的长调,他们三分钟就唱完了。”
“那不是笑话吗?”
“没人觉得可笑,都觉得理所当然。”
“那你呢,也觉得理所当然么?”
“我不知道。”
“你别回城了,城里虽然有不少好东西,但你想想,结婚时唱三天的歌都只唱三分钟,可以想象其他的一些事情了,你喜欢那个地方吗?你现在还能唱那段格萨尔进雨果(暗村)的故事么?”
扎西张口就唱,好多词他却唱不出来。
曲珍摇摇头,说:“看看你,不会唱了吧,现在有个什么节日,村里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有些仪式根本完成不了。就拿结婚时唱三天的长调来说,以后这些老人不在了,谁来唱,谁来记住这些歌声。”
“总会有人记住的,也许并不需要我来记。”
“每个人都这么想,让大山来记住吧。”
曲珍的话无意间总会出现在扎西的脑海里。
“我要回家一趟,家里妹妹要结婚。”达娃回家参加妹妹的婚礼去了。达娃一走,扎西就让所有的服务员全都放假,他早就心情烦透了,自己也该放假了。
没事他就一个人坐在阳台的太阳伞下,放着录音机,听着曲珍的歌声,一天喝一壶酥油茶,饿了吃点糌粑,其他的什么都不做。他对曲珍的歌声越来越上瘾,从村里回来后,扎西的心不知道丢去什么地方了。只有听着曲珍的歌声时,才感觉踏实,稳重,可是踏实过后,又是骚动在心底痒痒。
“我这是怎么了。”
“老板,怎么不做生意了。开门啊。”
楼下有人在喊门,扎西才懒得搭理呢。张口就回答:“放假了,去别家吧。”
“扎西。扎西。”
扎西伸头一看。琼带着一个人站在门口呢。
见到熟人,扎西也有些不好意思,下楼开了大门,琼和她的客人来到阳台上喝茶。
琼的客人是位中年妇女。看上去就气质不凡,戴着一副大大墨镜。话语不多。
“这位是老板,扎西。这位是艺校的龙娜老师。”
藏族?扎西看了一眼那老师,怎么都不像嘛,这位老师看上去还有些影星的派头呢。
琼像只麻雀一样说个不停,当听说这几天这里不开张时,她不由很遗憾地说,那我让老师住其他地方了。说话间,琼拿起放在桌上的录音机。
星星,六字真言,五姓诸佛,万伞太阳带着沙沙的声音从小小的录音机里飘出来。琼和她的老师一下都听呆了。
龙娜摘掉墨镜,对扎西急切地说:“年轻人,你在哪里找的音乐,能不能卖给我?”
怎么能卖。“不能卖,不能卖。”扎西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正要从琼手中拿回自己的录音机。但他抬头一看龙娜时,吓坏了。这个龙娜怎么和曲珍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龙娜显然不认识扎西。
“真没想到,有人会唱神川热巴。我找遍整个藏区,一直没找到。但能听到也是福气了。”龙娜一脸虔诚地听着。
龙娜是不是曲珍的母亲呢,如果是,她怎么连曲珍的歌声都听不出来。扎西话都不会说了。坐了会儿,琼带着龙娜走了。
龙娜走路的步伐和扎西以前见到的一样,只是热巴鼓已经不在她的背上,黄昏的夕阳射着石板路,龙娜的身上已经没有光芒,扎西看到的只是一个中年妇女的背影。
扎西真想追上去告诉龙娜,这是谁唱的歌,并把录音机送给龙娜,刚要举手喊龙娜,达娃站在扎西面前兴高采烈地喊到:“我回来了。”
达娃回来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发生了争吵,达娃对扎西很不满意,居然放假关门。
扎西说:“什么民族文化,饮食文化,你懂个屁,你读过多少书。你不就一个村姑。”达娃也适当地说出了那句话:“你这个盗卖文物的痞子。”达娃知道那一句话对扎西是致命伤害。
话说出来,两人才知道已经不能收回去了,相互对望着,不由想起这些年一起走过的岁月,两人才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两个人一起吃的苦头。
第二天,两人起床后,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但一下客气起来。达娃叫扎西吃早点,当扎西接过达娃手中的糌粑和酥油茶碗时,忍不住说了声:“谢谢。”除了一些客气生硬的话,两人之间还是沉默。
琼来了。她一进来,就大大咧咧地自己倒茶喝,抓起桌上的东西就吃。
“累死了,刚去机场把老师送走。”扎西才发现自己已经沉闷了很长时间,这个小城居然都通飞机了,他今天才知道。
琼从背包里拿出一部相机递给扎西:“这是老师让我给你,她说你知道的。
达娃已经开始脸色不对了。扎西也一头雾水:“我知道什么。龙娜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她知道那歌声是她的女儿曲珍唱的了?但给我一个相机又是什么意思。
琼赖皮地对扎西说着:“我的任务完成了,再让我听一次那歌声,好不好。
“不行。”扎西放下相机就走了出去。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拿出怀中的录音机。平时想放就放的歌声,扎西今天觉得很紧张,那按键好半天都没按下去。“我这是怎么了。”
扎西连连在心里默念着六字真言。一遍又一遍,终于心慢慢平静了。他又拿起录音机,听曲珍的歌。
沙……沙……只有一片空白。扎西不明白怎么了,怎么只有沙沙的空白声音,他前进了一段,还是沙沙的声音。他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歌声被人洗掉了。 扎西冲进厨房里,大声叫道:“达娃,你干什么了。”
达娃正兴高采烈地和琼聊着什么,两人靠那么近,一下被冲进门的扎西吓了一跳,琼话都不敢说了。达娃强作镇定地说:“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我的录音机里的歌声呢?到哪里去了。”
原来是这个啊,达娃松了一口气,她嘴巴一撇,说:“你那个录音机我怎么知道,昨天到今天我一直没动过,录音机不是一直在你的怀中吗?难道你自己搞坏的东西要赖到我头上不成。”
没等达娃把话说完,扎西又冲了出去。他手中紧紧地抓着那个录音机,心里想着,怎么就没有了,怎么就没有了。当他冲到房子对面的山坡上坐下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当扎西回到房间时,琼已经走了。达娃还是不和扎西说话,扎西拿起放在桌上的相机,心里想着,为什么龙娜给自己留一个相机,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和曲珍又有什么关系?曲珍的歌声怎么会消失,与龙娜有关吗?
“咔嚓!”不小心按到快门。这声音扎西一听就喜欢上了。现在他讨厌那些天天能听到的流行音乐,讨厌那些城市里的噪音。但清脆的快门声他一听就喜欢上了。
这相机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扎西开始研究手里的这个东西,他发现透过镜头,看到另一个世界,不,是世界的另一面。扎西感到相机把他的另一双眼睛打开了。
只是,只是他再去乡下时,什么生意都做不成了。当面对乡下人时,他更多的是举起手中的相机。照片就是和眼睛所能看到的不同。但扎西学着通过镜头来看世界后,他再不能用廉价的钱财从淳朴的乡下人手中换回好东西,他已经开不了口。更多的时候,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些事,一些人,他也开始一些思考。
农民摄影家。有人这样称呼他。
达娃和琼这段时间有点鬼鬼祟祟。琼本来是和扎西聊得好,现在却是和达娃聊上了。两个女孩本来聊得兴高采烈的,但见到扎西时,总会装得若无其事。“哼,小把戏。”扎西难道还看不出来。但他已经和达娃越来越远了。除了同住在一个院子里。
达娃经常和琼出去。现在饮食的生意达娃让她的表妹来帮忙,她并不用天天守在那里。有时达娃经常几天不见身影。 "
扎西也经常出去,拿着相机到处走。又回到以前的日子了,但再没有人叫他“藏狼扎西”了。从雪线到极地,从极地到无人区,扎西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走。他已经快走遍藏区。他不停地走着,吃很少的东西,也很少休息。不停地走,不停地走,顺着亘古不变的铃声,走过漫黄的冬日,赤足走过藏家的土掌房,沿着五彩斑斓的霞光,走进心中的极地,顺着千年不变的涛声,走过灿黄的秋日。
扎西好像走进了无时的岁月。这天,他来到一个地方,只看到大山一座连着一座,山底下的江静静地流淌,没有一点点绿色的大山看上去一片死寂,只有游荡的太阳发出刺眼的光芒。怎么和自己长大的那个村一样,扎西以为他回到了村里,但没有房屋,没有人。扎西以为自己看到了幻景,但真的是一模一样。扎西奔跑起来。
还是太阳当顶,风吹过后,雨点急急地下来了,雷声一个接一个在扎西的头顶炸开。快跑,快跑。一脚踩空的扎西从山上落下,直接掉入江水。
终于来了。
在身体坠落的瞬间,扎西忽然心就安稳了,从他开始出走的那个早晨,遇到达娃,曲珍的歌声,龙娜的背影,一幕幕地回放在扎西的眼前。扎西张开怀抱,拥抱大江。
身子终于重重地落在江面上。扎西最后一眼看着天空。再见了。
多吉老人正从天上飞过。这个传说中的飞人,终于飞起来,扎西见到多吉老人,笑了起来。老人张开的双手下,缓缓落下两朵莲花,莲花托着扎西,慢慢来到岸边。
“怎么回事。”扎西也被搞晕了。他看了看怀中的手机。试着拨通达娃的电话。电话通了。达娃在另一头乱哄哄的。扎西对着电话说:“我很想你。”达娃开心地在电话里说:“快回来吧。”被水浸泡的手机马上没声音了,扎西愤愤地把手机丢进大江。
江水还是一遍遍拍打着大山,岸边不断地泛起水泡,又消失,又起来。
“我该回村了。”
还没进屋子,就听到琼的声音,话语中还有曲珍的名字。扎西站在窗外,静静地听着。
“真可惜,这丫头不合作,我们该怎么逼她来合作呢。”
“曲珍好像和扎西特别要好的,能不能从扎西那边入手?”
“对啊,以前扎西的录音机里的歌声就是曲珍的。”
“不能让别人抢在我们前头。不然就坏了。”
“趁别人知道得还不多。怪不得龙娜不多说什么就走了。”
扎西在外面一句一句听明白了。
原来曲珍唱的是一首失传两千多年的热巴舞曲,或许这个世界上能唱热巴的只有曲珍一个人了。她就是一块活化石。
“你们两个如果在打曲珍的主意,别怪我不客气了。”扎西一字一句地把话钉在达娃和琼的心里。
回村了,同出走前一样,扎西身边什么都没有。甩着两只手,空荡荡的。
曲珍已经不在家了。
大山顶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寺院,山顶的寺院在人眼中显得特别小,红得晃人眼,挂在大山的额头。
“回村里吧。”
“不回去了。我怕我在村里呆下去,唱不出歌来,我的心里已经放入了好多东西。我不想再看了。”
每个星期,扎西都会上山给曲珍送一些生活用品及吃的。但曲珍从不见他,每次,扎西把东西放在大门口就回了。
扎西在回村才知道,多吉老人去世了。而且他去世的时候,飞起来过,全村人都见到了。多吉老人在一个山洞里修炼了四十九天,飞出了山洞。
“肯定是功力不够,刚飞出来,就掉进江了。”村人这样给扎西描述。
扎西想对曲珍说,他看到多吉老人了。曲珍在寺院的墙内说:“他到另一个世界了。”
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可一切又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
村里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外出,公路修到家门口,电话拉进了每家每户。
只是村里的一些男人们,喝酒时,还是会眼睛呆呆地盯着墙唱到:“古老的八角街上,窗户比门还多,窗户的姑娘们,骨头比肉还软。”这个时候,总会有人说,可惜了,曲珍的歌声。伴随着话语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扎西像只是跑出去过一天,或者没出去一样。还是放羊。偶尔会去多吉老人的房前转转。
有一天,刚到多吉老人的房前,扎西的大脚趾碰在一块尖石上,“哎哟!”扎西忍不住张开嘴吸着丝丝的冷气,他弯下腰去用手捂住脚,只看到已经快破的黄胶鞋,此时开了个大口子,而那块撞到脚的石块,上面写满了六字真言。扎西心里不无恶意地嘀咕,又是这个臭老头的石块。
这次,扎西拿起石块认真地看起来,他看到,在六字真言之间,大大地写着几个字:总得有人来讲述历史。
扎西耸耸肩,他细心地把石块上的尘埃用手袖抹干净,把石块用力丢进大山脚下的大江。
他心里想着:“或许,我该有个儿子了。”
石块在大江中,泛起一小片水花,水花又被后来的流水冲散了。江水依然安静。
江水下埋藏着多少故事啊。荒诞的,真实的,哀伤的,缠绵的,愤怒的,都已经慢慢被人们忘记,只有江水和大山记住了这些故事,当有了新故事时,江水又一遍一遍拍打着大山,大山之间又响起六字真言。
当掌物人摊开手心,大家看到了,曲珍佩带着的绿松石展现在大家面前。
“曲珍。”
“啊。”
曲珍一把抢过自己的绿松石,就跑开了。
孩子们已经站了起来,围着扎西一起进了村子,扎西的行李也都被孩子们分担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和扎西不停地说着话。
扎西年迈的父母见到扎西,一点也不惊奇,他们好像已经早就料到这一天。
回到村里好多天了,扎西一直没见到曲珍。扎西的耳边可没少听别人说起曲珍的种种事情,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曲珍的歌声。
多吉老人还是不停地在石板上刻着东西。
要离开的头一个晚上,扎西听到曲珍坐在窗台上唱歌了。他赶紧跑到曲珍家楼下。
曲珍不看他,自己唱着歌。
听着曲珍的歌曲,扎西心里被什么东西撕扯着,全身上下都不自在,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的感受了。“曲珍,别唱了。”
月光下,曲珍自己唱着,扎西在曲珍的歌声中好像看到一个远古的世界,大块块的石头,连绵不绝的海水,隆起的山脉。扎西走进了一个时间走廊。
扎西抱起自己的头。
最后一声鼓点停了下来,扎西的心也跟着舒坦了。
“干嘛,见我满脸都是皱皱,这么难受啊。”
曲珍变了,变调皮了。
“嗯,不是,嗯,是……”扎西结结巴巴的,他还在为刚才歌声中的世界所迷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曲珍跳下了窗台,站到扎西面前。用手比画了一下扎西的个子,继续说着:“我都有你高了哦。”
“嘿嘿。”
“长大了做我的媳妇。”
“你太讨厌了。”
“哼,你像只小鸟,赶紧长大,不然不要你了。”
“才不想理你。”
“你脸上怎么黑黑的,唉,是一牛屎啊。”
“呜……”
从小扎西就这么逗曲珍。现在却是扎西不知道说什么。回村里来,他最想见的就是曲珍。
“城里的日子怎么样?”
“很好啊。”
“怎么个好?”
“好多好东西呢。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城里的月亮比这个的亮么?”
“亮啊,又大又亮。”扎西话才说话,就被曲珍的鼓重重地敲在了头上。
“看你,吃的糌粑都还没拉干净,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了。”
“呵。”
时间从未向前走,也未曾过去,两个人笑着望着对方。
曲珍的眼睛转了转。又问:“那,那城里的姑娘漂亮么。”
“丑啊,都没你漂亮。”
曲珍开心地笑了起来。
“曲珍,你想过出去么?”
“为什么要出去?”
“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你干嘛还留在这里?”
“干嘛留在这里?”
“嗯。”
“这里有什么不好?”
曲珍纯真的话语带着小孩子的狡黠,让扎西回答不出来,感觉这么多年的好口才真是白用了。
“我阿爸让我好好唱歌,他说我在唱一个秘密。”
一阵咳嗽声从屋子里传出来,曲珍对着扎西吐了吐舌头。
“我要进去了。”曲珍转身就进了家门。
扎西还是像以前一样怕多吉老人,多吉老人见到扎西一句话都不说,头一扭就转开了,像村里的好多老人一样,扎西不明白,他怎么就把村里的老人全都得罪了。他带回来的礼物也被老人们拒绝了。
“老家伙。”扎西在心里不无恶意地暗暗称呼这些老人。
村里一些人家有了电视,那是在外打工的青年给家里买来的。
扎西也给家里买了电视,录像机,还有接受信号的天锅,可他发现父母根本不想多看那些玩意。
“哦,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才好。总不能和菩萨放在一起吧。”
试着放了几天的电视,就这么被放置到柴房里。
永格村是一个最蔑视现代化的村庄,外来的洋东西在这里都成了垃圾或者比垃圾还没用的东西。
反正每家的房子都很大,房子里放不下,放在院子里也行。
在外面那么一些年,扎西总在梦中回到村里,可现在他在村里却找不到位置。父母什么农活也不让他做,他天天就在村里东逛逛,西逛逛。
“曲珍长大了,曲珍已经二十二岁了。”
扎西的父母不停地在他耳边说着这个话,扎西怎么能不明白父母的意思呢。
“给你的。”
“这是什么?”
扎西摆弄着手里的录音机:“你说两句话。”
曲珍歪着头看着。“哩哩啦啦……哩哩啦啦。”
“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录音机里沙沙地重复着刚才曲珍发出的声音。
“啊,什么东西,在学我吗?”
“这是录音机。”
“录音机?”
“对,比如你唱什么,就可以录下来。很好玩吧。”
曲珍拿起录音机翻来覆去地看着,想看出点什么名堂。
“记录什么呢?”
“比如你的歌声。”
“歌声?”
“对。你不是说你在唱一个秘密吗,把它记录下来。”
“我不要。我的歌声在我心里呢,跑不掉。”曲珍把录音机还给扎西。想了想,她又拿起录音机来。“真能录下来吗?”
扎西点着头。曲珍说了一声,你等等我,就走开了。 "
过了一会儿,曲珍又来了。她拿起手鼓,换上平时节日里才穿的华贵的盛装。扎西想不明白曲珍要做什么。“把我的歌声录下来,留在你身边。放在怀里。”
曲珍开始唱歌了。扎西又看到那片大海,那崛起的山脉。他的脸跟着歌声变得龇牙咧嘴。曲珍用鼓棒重重地敲着扎西的头说:“看看你的表情。我怎么唱得下去。”
扎西好不容易调整一个笑容出来:“这样行吧。”
“哼,比哭还难看,真应该拿泡牛屎糊到你的脸上。”顺着曲珍的话,扎西深深地呼吸了口气,双手在脸上一抹:“糊上了。现在你可以唱歌了。”
从星星开始,到六字真言,到五姓诸佛,到神山,到万伞太阳,到纳福……曲珍唱得昏天黑地。从黄昏唱到天黑,从天黑唱到天亮,鼓点也一直响起。直到唱完,曲珍像生病一样脸色苍白,扎西也听得脸色苍白。
曲珍是仙女。扎西心里蹦出这个念头。
扎西再不敢起带曲珍离开这里的念头了。但他已经在村里留不住了。
旅游的热潮悄悄靠近了小城,OK厅的生意也越来越糟糕。
各类咖啡厅、酒吧、西餐馆在街上多起来。达娃坐不住了,她已经敏感地嗅到隐藏在小城里的种种气息,那股气息在召唤着她。
分析种种利弊后,达娃做了决定,搞餐饮文化。买地,起房子,装修,还是达娃一贯的风格,风风火火。扎西根本不用插手,但花的大部分都是他的积蓄,他心里不免有些心疼。
“达娃,你要折腾什么。”
“人就是要不断地向前走。还记得我们刚到这里时么,如果不是你先折腾,也许我们还在工地呢,所以折腾是好事。
“可是我累了。我不想做那么多事情。”
“不用你做,你闲着吧。我来折腾。”
从村里回城后,扎西一次都没出门。他感到自己生病了。
也正像达娃所说的一样,她根本不需要扎西来帮忙,在城里这么多年,因为后来的OK厅,达娃认识了很多的人,单位上的,社会上混的,做生意的,而且都关系不赖。
很快,房子起好了。
标准的藏式房,高高的三层,大大的院子,本来在二楼的厨房搬到院子里,围墙上一圈都放上了太阳伞,可以喝茶,一楼是餐厅,二楼是客房,三楼还是客房。
达娃的眼光果然不错。开张以来,生意一直不错。一批接一批的客人。每天都是满满的。达娃更忙了。扎西没什么事情可做,每天看碟子,喝酒。
“城里的人生活是怎么样的。”
“都一样的,但他们不做活。”
“不做活,那靠什么吃饭。”
“或者是做活的吧,反正不用种田,也不用放羊。”
“城里的人唱歌吗?”
“嗯,城里的人可喜欢唱歌了,还喜欢喝酒。”
“那不是和我们这里一样嘛。”
“也不一样,比如结婚时,我们唱的歌他们也唱,但好像很短很短。”
“很短很短?”
“比如我们祈福的三天的长调,他们三分钟就唱完了。”
“那不是笑话吗?”
“没人觉得可笑,都觉得理所当然。”
“那你呢,也觉得理所当然么?”
“我不知道。”
“你别回城了,城里虽然有不少好东西,但你想想,结婚时唱三天的歌都只唱三分钟,可以想象其他的一些事情了,你喜欢那个地方吗?你现在还能唱那段格萨尔进雨果(暗村)的故事么?”
扎西张口就唱,好多词他却唱不出来。
曲珍摇摇头,说:“看看你,不会唱了吧,现在有个什么节日,村里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有些仪式根本完成不了。就拿结婚时唱三天的长调来说,以后这些老人不在了,谁来唱,谁来记住这些歌声。”
“总会有人记住的,也许并不需要我来记。”
“每个人都这么想,让大山来记住吧。”
曲珍的话无意间总会出现在扎西的脑海里。
“我要回家一趟,家里妹妹要结婚。”达娃回家参加妹妹的婚礼去了。达娃一走,扎西就让所有的服务员全都放假,他早就心情烦透了,自己也该放假了。
没事他就一个人坐在阳台的太阳伞下,放着录音机,听着曲珍的歌声,一天喝一壶酥油茶,饿了吃点糌粑,其他的什么都不做。他对曲珍的歌声越来越上瘾,从村里回来后,扎西的心不知道丢去什么地方了。只有听着曲珍的歌声时,才感觉踏实,稳重,可是踏实过后,又是骚动在心底痒痒。
“我这是怎么了。”
“老板,怎么不做生意了。开门啊。”
楼下有人在喊门,扎西才懒得搭理呢。张口就回答:“放假了,去别家吧。”
“扎西。扎西。”
扎西伸头一看。琼带着一个人站在门口呢。
见到熟人,扎西也有些不好意思,下楼开了大门,琼和她的客人来到阳台上喝茶。
琼的客人是位中年妇女。看上去就气质不凡,戴着一副大大墨镜。话语不多。
“这位是老板,扎西。这位是艺校的龙娜老师。”
藏族?扎西看了一眼那老师,怎么都不像嘛,这位老师看上去还有些影星的派头呢。
琼像只麻雀一样说个不停,当听说这几天这里不开张时,她不由很遗憾地说,那我让老师住其他地方了。说话间,琼拿起放在桌上的录音机。
星星,六字真言,五姓诸佛,万伞太阳带着沙沙的声音从小小的录音机里飘出来。琼和她的老师一下都听呆了。
龙娜摘掉墨镜,对扎西急切地说:“年轻人,你在哪里找的音乐,能不能卖给我?”
怎么能卖。“不能卖,不能卖。”扎西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正要从琼手中拿回自己的录音机。但他抬头一看龙娜时,吓坏了。这个龙娜怎么和曲珍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
龙娜显然不认识扎西。
“真没想到,有人会唱神川热巴。我找遍整个藏区,一直没找到。但能听到也是福气了。”龙娜一脸虔诚地听着。
龙娜是不是曲珍的母亲呢,如果是,她怎么连曲珍的歌声都听不出来。扎西话都不会说了。坐了会儿,琼带着龙娜走了。
龙娜走路的步伐和扎西以前见到的一样,只是热巴鼓已经不在她的背上,黄昏的夕阳射着石板路,龙娜的身上已经没有光芒,扎西看到的只是一个中年妇女的背影。
扎西真想追上去告诉龙娜,这是谁唱的歌,并把录音机送给龙娜,刚要举手喊龙娜,达娃站在扎西面前兴高采烈地喊到:“我回来了。”
达娃回来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发生了争吵,达娃对扎西很不满意,居然放假关门。
扎西说:“什么民族文化,饮食文化,你懂个屁,你读过多少书。你不就一个村姑。”达娃也适当地说出了那句话:“你这个盗卖文物的痞子。”达娃知道那一句话对扎西是致命伤害。
话说出来,两人才知道已经不能收回去了,相互对望着,不由想起这些年一起走过的岁月,两人才到这个城市时的情景,两个人一起吃的苦头。
第二天,两人起床后,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但一下客气起来。达娃叫扎西吃早点,当扎西接过达娃手中的糌粑和酥油茶碗时,忍不住说了声:“谢谢。”除了一些客气生硬的话,两人之间还是沉默。
琼来了。她一进来,就大大咧咧地自己倒茶喝,抓起桌上的东西就吃。
“累死了,刚去机场把老师送走。”扎西才发现自己已经沉闷了很长时间,这个小城居然都通飞机了,他今天才知道。
琼从背包里拿出一部相机递给扎西:“这是老师让我给你,她说你知道的。
达娃已经开始脸色不对了。扎西也一头雾水:“我知道什么。龙娜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她知道那歌声是她的女儿曲珍唱的了?但给我一个相机又是什么意思。
琼赖皮地对扎西说着:“我的任务完成了,再让我听一次那歌声,好不好。
“不行。”扎西放下相机就走了出去。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拿出怀中的录音机。平时想放就放的歌声,扎西今天觉得很紧张,那按键好半天都没按下去。“我这是怎么了。”
扎西连连在心里默念着六字真言。一遍又一遍,终于心慢慢平静了。他又拿起录音机,听曲珍的歌。
沙……沙……只有一片空白。扎西不明白怎么了,怎么只有沙沙的空白声音,他前进了一段,还是沙沙的声音。他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歌声被人洗掉了。 扎西冲进厨房里,大声叫道:“达娃,你干什么了。”
达娃正兴高采烈地和琼聊着什么,两人靠那么近,一下被冲进门的扎西吓了一跳,琼话都不敢说了。达娃强作镇定地说:“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我的录音机里的歌声呢?到哪里去了。”
原来是这个啊,达娃松了一口气,她嘴巴一撇,说:“你那个录音机我怎么知道,昨天到今天我一直没动过,录音机不是一直在你的怀中吗?难道你自己搞坏的东西要赖到我头上不成。”
没等达娃把话说完,扎西又冲了出去。他手中紧紧地抓着那个录音机,心里想着,怎么就没有了,怎么就没有了。当他冲到房子对面的山坡上坐下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当扎西回到房间时,琼已经走了。达娃还是不和扎西说话,扎西拿起放在桌上的相机,心里想着,为什么龙娜给自己留一个相机,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和曲珍又有什么关系?曲珍的歌声怎么会消失,与龙娜有关吗?
“咔嚓!”不小心按到快门。这声音扎西一听就喜欢上了。现在他讨厌那些天天能听到的流行音乐,讨厌那些城市里的噪音。但清脆的快门声他一听就喜欢上了。
这相机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扎西开始研究手里的这个东西,他发现透过镜头,看到另一个世界,不,是世界的另一面。扎西感到相机把他的另一双眼睛打开了。
只是,只是他再去乡下时,什么生意都做不成了。当面对乡下人时,他更多的是举起手中的相机。照片就是和眼睛所能看到的不同。但扎西学着通过镜头来看世界后,他再不能用廉价的钱财从淳朴的乡下人手中换回好东西,他已经开不了口。更多的时候,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些事,一些人,他也开始一些思考。
农民摄影家。有人这样称呼他。
达娃和琼这段时间有点鬼鬼祟祟。琼本来是和扎西聊得好,现在却是和达娃聊上了。两个女孩本来聊得兴高采烈的,但见到扎西时,总会装得若无其事。“哼,小把戏。”扎西难道还看不出来。但他已经和达娃越来越远了。除了同住在一个院子里。
达娃经常和琼出去。现在饮食的生意达娃让她的表妹来帮忙,她并不用天天守在那里。有时达娃经常几天不见身影。 "
扎西也经常出去,拿着相机到处走。又回到以前的日子了,但再没有人叫他“藏狼扎西”了。从雪线到极地,从极地到无人区,扎西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走。他已经快走遍藏区。他不停地走着,吃很少的东西,也很少休息。不停地走,不停地走,顺着亘古不变的铃声,走过漫黄的冬日,赤足走过藏家的土掌房,沿着五彩斑斓的霞光,走进心中的极地,顺着千年不变的涛声,走过灿黄的秋日。
扎西好像走进了无时的岁月。这天,他来到一个地方,只看到大山一座连着一座,山底下的江静静地流淌,没有一点点绿色的大山看上去一片死寂,只有游荡的太阳发出刺眼的光芒。怎么和自己长大的那个村一样,扎西以为他回到了村里,但没有房屋,没有人。扎西以为自己看到了幻景,但真的是一模一样。扎西奔跑起来。
还是太阳当顶,风吹过后,雨点急急地下来了,雷声一个接一个在扎西的头顶炸开。快跑,快跑。一脚踩空的扎西从山上落下,直接掉入江水。
终于来了。
在身体坠落的瞬间,扎西忽然心就安稳了,从他开始出走的那个早晨,遇到达娃,曲珍的歌声,龙娜的背影,一幕幕地回放在扎西的眼前。扎西张开怀抱,拥抱大江。
身子终于重重地落在江面上。扎西最后一眼看着天空。再见了。
多吉老人正从天上飞过。这个传说中的飞人,终于飞起来,扎西见到多吉老人,笑了起来。老人张开的双手下,缓缓落下两朵莲花,莲花托着扎西,慢慢来到岸边。
“怎么回事。”扎西也被搞晕了。他看了看怀中的手机。试着拨通达娃的电话。电话通了。达娃在另一头乱哄哄的。扎西对着电话说:“我很想你。”达娃开心地在电话里说:“快回来吧。”被水浸泡的手机马上没声音了,扎西愤愤地把手机丢进大江。
江水还是一遍遍拍打着大山,岸边不断地泛起水泡,又消失,又起来。
“我该回村了。”
还没进屋子,就听到琼的声音,话语中还有曲珍的名字。扎西站在窗外,静静地听着。
“真可惜,这丫头不合作,我们该怎么逼她来合作呢。”
“曲珍好像和扎西特别要好的,能不能从扎西那边入手?”
“对啊,以前扎西的录音机里的歌声就是曲珍的。”
“不能让别人抢在我们前头。不然就坏了。”
“趁别人知道得还不多。怪不得龙娜不多说什么就走了。”
扎西在外面一句一句听明白了。
原来曲珍唱的是一首失传两千多年的热巴舞曲,或许这个世界上能唱热巴的只有曲珍一个人了。她就是一块活化石。
“你们两个如果在打曲珍的主意,别怪我不客气了。”扎西一字一句地把话钉在达娃和琼的心里。
回村了,同出走前一样,扎西身边什么都没有。甩着两只手,空荡荡的。
曲珍已经不在家了。
大山顶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寺院,山顶的寺院在人眼中显得特别小,红得晃人眼,挂在大山的额头。
“回村里吧。”
“不回去了。我怕我在村里呆下去,唱不出歌来,我的心里已经放入了好多东西。我不想再看了。”
每个星期,扎西都会上山给曲珍送一些生活用品及吃的。但曲珍从不见他,每次,扎西把东西放在大门口就回了。
扎西在回村才知道,多吉老人去世了。而且他去世的时候,飞起来过,全村人都见到了。多吉老人在一个山洞里修炼了四十九天,飞出了山洞。
“肯定是功力不够,刚飞出来,就掉进江了。”村人这样给扎西描述。
扎西想对曲珍说,他看到多吉老人了。曲珍在寺院的墙内说:“他到另一个世界了。”
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可一切又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
村里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外出,公路修到家门口,电话拉进了每家每户。
只是村里的一些男人们,喝酒时,还是会眼睛呆呆地盯着墙唱到:“古老的八角街上,窗户比门还多,窗户的姑娘们,骨头比肉还软。”这个时候,总会有人说,可惜了,曲珍的歌声。伴随着话语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扎西像只是跑出去过一天,或者没出去一样。还是放羊。偶尔会去多吉老人的房前转转。
有一天,刚到多吉老人的房前,扎西的大脚趾碰在一块尖石上,“哎哟!”扎西忍不住张开嘴吸着丝丝的冷气,他弯下腰去用手捂住脚,只看到已经快破的黄胶鞋,此时开了个大口子,而那块撞到脚的石块,上面写满了六字真言。扎西心里不无恶意地嘀咕,又是这个臭老头的石块。
这次,扎西拿起石块认真地看起来,他看到,在六字真言之间,大大地写着几个字:总得有人来讲述历史。
扎西耸耸肩,他细心地把石块上的尘埃用手袖抹干净,把石块用力丢进大山脚下的大江。
他心里想着:“或许,我该有个儿子了。”
石块在大江中,泛起一小片水花,水花又被后来的流水冲散了。江水依然安静。
江水下埋藏着多少故事啊。荒诞的,真实的,哀伤的,缠绵的,愤怒的,都已经慢慢被人们忘记,只有江水和大山记住了这些故事,当有了新故事时,江水又一遍一遍拍打着大山,大山之间又响起六字真言。
相关推荐
拉萨河文化生态保护区申报进入冲刺阶段
“十一五”期间,文化部确定要在全国建设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目前,全国已建设4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也就是说,2010年作为“十一五”的最后一年,还有6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
2010-07-16 编辑:admin 5731青藏国际旅行社海南州分社举行揭牌仪式
张文魁州长和宁克平副州长为旅行社开业揭牌 6月18日,青藏国际旅行社海南州分社揭牌仪式在海南州青海湖广场隆重举行。海南州政府张文魁州长和宁克平副州长为旅行社开业揭牌。 海南州旅游局局长才让多杰致词 张文魁州长等一行领导参观海南分社 青藏国际旅行社...
2011-06-23 编辑:admin 5483藏乐飘飘 星光熠熠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歌手活跃在大众舞台上,如迈克·杰克逊和邓丽君等歌坛巨星,他们已经成为时代的坐标,在全世界亿万乐迷心中他们的歌声是永恒的,那些经典的旋律已经烙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而藏族歌手作为其中一小部分群体,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同样也被我们铭记心中...
2009-08-17 编辑:admin 9838阿顿·华多太最新诗作
依拉,那地方 阿顿·华多太 香格里拉依拉草原 这个被称为依拉的地方 其实是一片草原 也是一座山 我们走到山上 让风朗读经幡上的诗词 ...
2013-11-19 编辑:admin 6028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