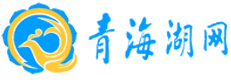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青海湖的眼睛》上卷之第一节
作者:千年风铃
来源:青海湖网
时间:2010-01-08 11:35:39
点击数:

他竭力睁大双眼,向四处张望,但四下里迷雾重重,什么也看不见。他瑟瑟缩缩的往前走,猛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两个人影从迷雾中显出身来,向他缓缓走来。那两个人的面貌渐渐地变得清晰了,竟是他的父母亲。父亲面容青紫,血渍满布,母亲面上尽是绝望的神色。他惊骇地大叫:“爸,妈!你们——”但父母亲却不应声,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想哭,可就是哭不出声来,就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的声音堵在他的喉咙里一样,憋得他难受得要命。少顷,他看见父母亲同时向他淡淡地一笑,那笑是那样惨淡,令他心碎。他向他们跑去,伸出手去想要拉他们,但他们突然消失在迷雾中,无影无踪了。他惊恐地向四周张望,觉得身体渐渐变得冰凉,像是浸在一片深不可测的海水中,正缓缓往下沉,越来越深,越来越冷。
他从睡梦中猛地惊醒,一下地坐了起来,气息粗重,额上尽是湿湿的冷汗。他心怀着梦里的那种恐惧,往四下里张望。恍惚中,他看见街上的灯光显得扑朔迷离,建筑物的黑影隐隐绰绰的在浓浓的夜幕中矗立着。他感觉刚才那迷雾弥漫的梦境似乎是这个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父母亲正幽幽地飘浮在那茫茫夜空中的某个地方,正在看着他,用的正是他刚才在梦中所见到的那种眼神和表情。他吓得不敢再抬头往远处看了,将颤抖不停的身体往后挪了挪,背靠着体育馆的冰冷的墙壁坐着,双臂抱膝,蜷成了一团。他分不清那种令他恐惧异常的寒冷到底是从刚才那睡梦中产生的,还是从这沁凉的夜色中产生的。睡意犹在,迷迷糊糊中,他只觉得那冰冷浸入了骨髓,在身体的深处一点一点地凝结了起来。
五月初的西宁,天气还是很凉的,尤其是在临晨这段时间,更别说正在下雨了。湿冷的空气中夹杂着城市所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腐烂的腥味。广场上和街道上的灯在雨雾中显得昏暗疲倦,汽车像是穿越重重迷雾的幽灵一样,在远处的街道上无声无息地行驶。高大的建筑物那幽暗的黑影在迷蒙的夜空中怪诞地扭曲着。细雨还在无声无息地落着,湿冷的空气里酝酿着一种沉郁惨淡的气氛。他背靠着建筑物的冰冷的墙壁,屁股下坐着的是冰凉的水泥地面,浓浓的寒意不断地向他袭来,使他浑身止不住一阵阵的颤抖。他吸着冷气,用力躬着身子,将整个身体紧紧地蜷缩在一起。
寒冷驱走了睡意,他的意识变得清醒了。他回想着刚才的梦,回想着他在梦中看到的父母亲的样子,竟与他痛苦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变得异常的清晰,仿佛他们就立在眼前。恐惧又袭来,他连忙闭上了双眼。他想将刚才梦中所见的那恐怖的情形、以及父母亲的可怖死状一起抛到脑后,但越是想忘记,却越来越清晰了,竟虚实相缠,交替往复,挥之难去。那在他的心里纠结了许久的疼痛在这恐惧的阴影中迅速地膨胀起来,揪心扯肺,并且向他的整个胸膛弥漫。他感到胸腔里一阵憋闷,那沉闷的疼痛似是在找一个出口,迅速地冲了上来,聚在他的喉咙里,再难上移。他感觉喉咙里一阵沉沉的闷疼,自己快要窒息而死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顺着冰凉的脸颊扑簌簌的滑落。
他抬起了头,往远处望去,泪眼模糊中,看见建筑物的黑影和广场上街道上的灯光都变得迷离不定,仿佛一群奇形怪状的妖魔在扭动着他们丑陋的肢体。
回忆又来骚扰他,往昔生活的剪影涌入他的脑海。
母亲生病多年,原本是可以治好的,但她一直拒绝去医院。他家里很穷,而他在读书。如果母亲去医院,那就意味着他要辍学了,这是父母亲所不愿意看到的。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了几十年。他的头脑不如村里别的男人们那样活络,不懂得经营谋生之道,更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对于时代的气息有着灵敏的嗅觉。当别人开始外出搞副业、做买卖时,他在那八亩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相同的工作:耕地、播种、收割,不知道厌烦,亦不知道疲倦,但是也没有什么激情。他也曾经学着人家搞过养殖,养了五只羊,但没过一年,有一只被偷,一只跑到人家地里吃麦苗时被打死了,一只被人家给赖了,他见大势已去,连忙将剩下两只卖了,得到的钱给妻子和儿子一人买了一身衣服,从此不再谈养殖。他也外出搞过副业,但是三个月的工资一分钱都没有到手,反而被人家诬他偷了东西,他为了清白打破了人家的头,被派出所拘留了两天,两手空空地回来。从那以后,他既不外出搞副业,也不在家搞养殖,只将那八亩地当作他的命根子,在那上面寻找全家的经济来源。
他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条件尚可,虽没有可供挥霍的钱,但吃穿倒是不用愁,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父亲满足于这种舒适而平淡的生活,连最后一点残存的进取心也消失殆尽。后来,他上了高中,家里就开始吃紧了。他在县城一中读书,一年下来,学费和其它的杂费、生活费是初中时的四倍。在他高二的时候,母亲又病了。父亲既要为母亲治病,还要供他上学。从那时起,家里那一点点收入再也没有个够的时候。后来,为了不耽误他读书,母亲就不再去医院看病了。他成了父母亲心里唯一的希望。母亲依然像往常一样劳作,从来不叫疼。他看到母亲的脸色越来越不好,身体也越来越消瘦,心里发急了,想出了辍学的主意,想省下钱来为母亲治病。但这样一来更糟,母亲因为又气又急,病情反而加重了,她不去医院的态度更坚决,连买来的药都不吃,并且以死来威胁他。他只好含着泪去学校。
三年后,高考失败,他心里不似别人那样又伤心又悲痛,反而全身心有说不出的轻松。他想自己终于可以出去挣钱给妈妈治病了。他准备痛痛快快地挨上父母亲的一顿教训后就出去挣钱。但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父母亲要他复读一年。他坚决地声明自己不想再去读书,但是,母亲又以死相威胁,逼得他只好同意了。
他又读了一年,但是他讨厌读书,他觉得读书对他来说是死死套在身上的一道枷锁,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心不在焉地在教室里坐着,觉得那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得太慢,慢得几乎让他发了疯。终于熬到了今年四月份,离高考不远了。学校里收资料费,父亲实在拿不出什么钱来,就拉着家里的粮食到县城去卖,想弄点钱给他交资料费。卖了粮食回来时,一辆拉沙子的东风汽车撞在了父亲拉着的架子车上,父亲被架子车的车辕挑飞了出去,掼在了马路边的一棵大白杨树上,脑袋被撞了个大窟窿。那一张张肮脏的零零碎碎的钞票在鲜血中扎眼地盖住了父亲的头脸,他满是血污的右手里还捏着一张破旧的伍拾圆大钞。瘦弱的母亲听到了父亲的死讯,突然栽倒在菜地里,再也没有醒过来。他看到母亲时,见母亲的双眼睁着,虽然早已淡而无神,但一丝绝望的微光依然像个幽灵一样在那两个淡黄的眼珠子里隐隐闪着。
他心里空空的,感觉不到疼痛。疼痛是在父亲和母亲的灵柩将要运往坟地时才产生的。那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疼痛刺得他死去活来。他泪眼模糊地睡了四五天,不吃也不喝,胸腔憋闷,喉咙痉挛,几乎透不过气来。处于绝望和悲痛的侵蚀之中,他的意识变得模糊不清,脑子里空空荡荡的,仿佛里面所有东西都被什么邪恶的精灵吸走了一样。父亲那鲜血满布的遗容和母亲那绝望的眼神就像锋利无比的匕首一样,在他的心里划出一道道的伤口来,疼痛无比。
世界在他的眼里突然变得那么的陌生,那么的冷漠无情。他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给抛弃了。他痛恨自己,于是,用不吃不喝的手段来惩罚自己。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要不是他,要不是为了他那几个破资料费,父亲就不会去县城卖粮食。要不是他,母亲可能早就看好了病,而不会拖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都是贫穷惹的祸。母亲生病不治,父亲为了几个钱去卖粮食,这都是因为家里穷。父母亲可怜的一生和他们悲惨的结局都是因为贫穷。他痛恨自己,更恨贫穷。他虽然对未来感到绝望和茫然,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但是,这种仇恨的情绪像杂草一样长在悲痛和绝望的麦田里,鲜嫩茁壮。他不再害怕,他知道以后要做什么。那种仇恨的情绪给了他力量和勇气,使他抛掉了胆怯和懦弱,使他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将来了。他发誓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
钱,现在成了他唯一渴求的东西。他二十二岁的柔软的心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金钱的外壳。他祈求父母亲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他,让他挣好多好多钱。
虽然他还不知道该怎样去挣钱,但是,他不想像父亲一样,在家里那没有任何希望的八亩地上白白地耗费自己的生命,他想和别人一样到外面打工。他听说同村那个叫裴炎林的在西宁打工,他便到他家里问了他的地址。他把家里收拾了一下,锁好了门窗,并且托邻居家的王婶帮忙照看一下他的家。他做好了所有的安排后,便来了西宁。
他照着裴炎林的家人给他的地址找去时,发现那儿是一家建筑工地。但他打听到裴炎林早已不在那里了。他一下地傻了眼,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但很快,他就明白,他非得快快的找一份工作不可。否则,既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吃的,他就坚持不了几天。他去了几家建筑工地,人家看他面孔稚嫩,连理都不理他。后来,他在一家不大也不小的饭店里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很是珍惜这第一份工作。十几天来,他都干得很卖力,老板娘和同事们好像都有点喜欢他了。但是,到了今天晚上,正是饭馆里人多的时候,他不小心滑倒在地,摔碎了五个碗,那个老板娘一生气,也不顾他的苦苦哀求,把他连推带搡地赶到大街上来了。那一刻,他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又流了泪。他感觉自己还不如那老板娘随手扔在马路上的那块破抹布。
他带着恐怖的心情看着陌生的街道。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一种深切的孤独的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痛苦地明白,自己今晚要露宿街头了。幸亏早些时候他在饭店里吃了一碗牛肉面,要不然的话,他还得化钱去买些吃的。他随着人流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着,不知不觉来到了中心广场上。他身心俱疲、悲痛满胸地坐在台阶上,茫然地看着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们跳舞唱歌,心里体味着辛酸和孤独。
在那个饭店里歇都没歇一下,忙了整整一天,他有点累了。他在那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坐了一会儿,觉得腰有些不舒服,看了看四下里,见附近没有人影儿,也不管地上脏不脏,便躺了下来。他仰望着那没有星辰的夜空,依然可以听到广场上轰天响的舞曲,唱歌声,依然可以看见人影在城市那华美的灯光中闪动着。他看着看着,意识渐渐地变得迷迷糊糊的。后来,他睡着了。
他睡得很沉,不知道什么时候广场上已经没有了音乐和歌声,也没有了人群,只剩下街灯的光寂寞地照亮着广场那灰暗的石板地面。他更不知道什么时候风静了下来,下起了雨来。雨顺着风势,急急地扑在他的身上,脸面上,他醒了过来。他连忙转移到了体育馆的廊檐下。
变化多快啊,白天还是个多么热闹的世界,街道上的人和车多得数不清,就像湟水河里的水一样在流。可是现在,仅仅只隔了几个小时,街上的行人不见了,来往的汽车也少得可怜,就连天气也变得又冷又湿。白天里的那些衣着又光鲜又时髦的人们此刻正睡在宽大柔软的床上,盖着温暖的被子,做着香甜的美梦。可是他呢,穿着单薄的衣服蜷在城市建筑物的冰冷的墙壁前,在冷风中瑟瑟的发抖,可怜的情状就和那过往的车辆扔在马路上的饮料瓶差不多。
一阵冷风扑面的吹来,把几滴冰凉的雨点吹到了他的脸上。他吸了一口冷气,把身体蜷缩得更紧了。这彻骨的寒冷让他的睡意完全消失了。他看着雨雾中那带着倦意的昏黄的街灯,它们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向暗夜中散发着一簇簇的光。高大的建筑物的黑影紧紧地挤在一起,使夜色更深更浓。
又是无尽的绵绵的悲痛,又是两行眼泪。他抬起头,模糊的双眼朝东望去,那里依旧是一片黑暗。
“明天会怎样呢?”他幽幽地想。
他从睡梦中猛地惊醒,一下地坐了起来,气息粗重,额上尽是湿湿的冷汗。他心怀着梦里的那种恐惧,往四下里张望。恍惚中,他看见街上的灯光显得扑朔迷离,建筑物的黑影隐隐绰绰的在浓浓的夜幕中矗立着。他感觉刚才那迷雾弥漫的梦境似乎是这个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父母亲正幽幽地飘浮在那茫茫夜空中的某个地方,正在看着他,用的正是他刚才在梦中所见到的那种眼神和表情。他吓得不敢再抬头往远处看了,将颤抖不停的身体往后挪了挪,背靠着体育馆的冰冷的墙壁坐着,双臂抱膝,蜷成了一团。他分不清那种令他恐惧异常的寒冷到底是从刚才那睡梦中产生的,还是从这沁凉的夜色中产生的。睡意犹在,迷迷糊糊中,他只觉得那冰冷浸入了骨髓,在身体的深处一点一点地凝结了起来。
五月初的西宁,天气还是很凉的,尤其是在临晨这段时间,更别说正在下雨了。湿冷的空气中夹杂着城市所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腐烂的腥味。广场上和街道上的灯在雨雾中显得昏暗疲倦,汽车像是穿越重重迷雾的幽灵一样,在远处的街道上无声无息地行驶。高大的建筑物那幽暗的黑影在迷蒙的夜空中怪诞地扭曲着。细雨还在无声无息地落着,湿冷的空气里酝酿着一种沉郁惨淡的气氛。他背靠着建筑物的冰冷的墙壁,屁股下坐着的是冰凉的水泥地面,浓浓的寒意不断地向他袭来,使他浑身止不住一阵阵的颤抖。他吸着冷气,用力躬着身子,将整个身体紧紧地蜷缩在一起。
寒冷驱走了睡意,他的意识变得清醒了。他回想着刚才的梦,回想着他在梦中看到的父母亲的样子,竟与他痛苦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变得异常的清晰,仿佛他们就立在眼前。恐惧又袭来,他连忙闭上了双眼。他想将刚才梦中所见的那恐怖的情形、以及父母亲的可怖死状一起抛到脑后,但越是想忘记,却越来越清晰了,竟虚实相缠,交替往复,挥之难去。那在他的心里纠结了许久的疼痛在这恐惧的阴影中迅速地膨胀起来,揪心扯肺,并且向他的整个胸膛弥漫。他感到胸腔里一阵憋闷,那沉闷的疼痛似是在找一个出口,迅速地冲了上来,聚在他的喉咙里,再难上移。他感觉喉咙里一阵沉沉的闷疼,自己快要窒息而死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顺着冰凉的脸颊扑簌簌的滑落。
他抬起了头,往远处望去,泪眼模糊中,看见建筑物的黑影和广场上街道上的灯光都变得迷离不定,仿佛一群奇形怪状的妖魔在扭动着他们丑陋的肢体。
回忆又来骚扰他,往昔生活的剪影涌入他的脑海。
母亲生病多年,原本是可以治好的,但她一直拒绝去医院。他家里很穷,而他在读书。如果母亲去医院,那就意味着他要辍学了,这是父母亲所不愿意看到的。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土地上劳作了几十年。他的头脑不如村里别的男人们那样活络,不懂得经营谋生之道,更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对于时代的气息有着灵敏的嗅觉。当别人开始外出搞副业、做买卖时,他在那八亩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相同的工作:耕地、播种、收割,不知道厌烦,亦不知道疲倦,但是也没有什么激情。他也曾经学着人家搞过养殖,养了五只羊,但没过一年,有一只被偷,一只跑到人家地里吃麦苗时被打死了,一只被人家给赖了,他见大势已去,连忙将剩下两只卖了,得到的钱给妻子和儿子一人买了一身衣服,从此不再谈养殖。他也外出搞过副业,但是三个月的工资一分钱都没有到手,反而被人家诬他偷了东西,他为了清白打破了人家的头,被派出所拘留了两天,两手空空地回来。从那以后,他既不外出搞副业,也不在家搞养殖,只将那八亩地当作他的命根子,在那上面寻找全家的经济来源。
他读初中的时候,家里条件尚可,虽没有可供挥霍的钱,但吃穿倒是不用愁,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父亲满足于这种舒适而平淡的生活,连最后一点残存的进取心也消失殆尽。后来,他上了高中,家里就开始吃紧了。他在县城一中读书,一年下来,学费和其它的杂费、生活费是初中时的四倍。在他高二的时候,母亲又病了。父亲既要为母亲治病,还要供他上学。从那时起,家里那一点点收入再也没有个够的时候。后来,为了不耽误他读书,母亲就不再去医院看病了。他成了父母亲心里唯一的希望。母亲依然像往常一样劳作,从来不叫疼。他看到母亲的脸色越来越不好,身体也越来越消瘦,心里发急了,想出了辍学的主意,想省下钱来为母亲治病。但这样一来更糟,母亲因为又气又急,病情反而加重了,她不去医院的态度更坚决,连买来的药都不吃,并且以死来威胁他。他只好含着泪去学校。
三年后,高考失败,他心里不似别人那样又伤心又悲痛,反而全身心有说不出的轻松。他想自己终于可以出去挣钱给妈妈治病了。他准备痛痛快快地挨上父母亲的一顿教训后就出去挣钱。但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父母亲要他复读一年。他坚决地声明自己不想再去读书,但是,母亲又以死相威胁,逼得他只好同意了。
他又读了一年,但是他讨厌读书,他觉得读书对他来说是死死套在身上的一道枷锁,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心不在焉地在教室里坐着,觉得那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得太慢,慢得几乎让他发了疯。终于熬到了今年四月份,离高考不远了。学校里收资料费,父亲实在拿不出什么钱来,就拉着家里的粮食到县城去卖,想弄点钱给他交资料费。卖了粮食回来时,一辆拉沙子的东风汽车撞在了父亲拉着的架子车上,父亲被架子车的车辕挑飞了出去,掼在了马路边的一棵大白杨树上,脑袋被撞了个大窟窿。那一张张肮脏的零零碎碎的钞票在鲜血中扎眼地盖住了父亲的头脸,他满是血污的右手里还捏着一张破旧的伍拾圆大钞。瘦弱的母亲听到了父亲的死讯,突然栽倒在菜地里,再也没有醒过来。他看到母亲时,见母亲的双眼睁着,虽然早已淡而无神,但一丝绝望的微光依然像个幽灵一样在那两个淡黄的眼珠子里隐隐闪着。
他心里空空的,感觉不到疼痛。疼痛是在父亲和母亲的灵柩将要运往坟地时才产生的。那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疼痛刺得他死去活来。他泪眼模糊地睡了四五天,不吃也不喝,胸腔憋闷,喉咙痉挛,几乎透不过气来。处于绝望和悲痛的侵蚀之中,他的意识变得模糊不清,脑子里空空荡荡的,仿佛里面所有东西都被什么邪恶的精灵吸走了一样。父亲那鲜血满布的遗容和母亲那绝望的眼神就像锋利无比的匕首一样,在他的心里划出一道道的伤口来,疼痛无比。
世界在他的眼里突然变得那么的陌生,那么的冷漠无情。他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给抛弃了。他痛恨自己,于是,用不吃不喝的手段来惩罚自己。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要不是他,要不是为了他那几个破资料费,父亲就不会去县城卖粮食。要不是他,母亲可能早就看好了病,而不会拖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都是贫穷惹的祸。母亲生病不治,父亲为了几个钱去卖粮食,这都是因为家里穷。父母亲可怜的一生和他们悲惨的结局都是因为贫穷。他痛恨自己,更恨贫穷。他虽然对未来感到绝望和茫然,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但是,这种仇恨的情绪像杂草一样长在悲痛和绝望的麦田里,鲜嫩茁壮。他不再害怕,他知道以后要做什么。那种仇恨的情绪给了他力量和勇气,使他抛掉了胆怯和懦弱,使他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将来了。他发誓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
钱,现在成了他唯一渴求的东西。他二十二岁的柔软的心被裹上了一层厚厚的金钱的外壳。他祈求父母亲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他,让他挣好多好多钱。
虽然他还不知道该怎样去挣钱,但是,他不想像父亲一样,在家里那没有任何希望的八亩地上白白地耗费自己的生命,他想和别人一样到外面打工。他听说同村那个叫裴炎林的在西宁打工,他便到他家里问了他的地址。他把家里收拾了一下,锁好了门窗,并且托邻居家的王婶帮忙照看一下他的家。他做好了所有的安排后,便来了西宁。
他照着裴炎林的家人给他的地址找去时,发现那儿是一家建筑工地。但他打听到裴炎林早已不在那里了。他一下地傻了眼,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但很快,他就明白,他非得快快的找一份工作不可。否则,既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吃的,他就坚持不了几天。他去了几家建筑工地,人家看他面孔稚嫩,连理都不理他。后来,他在一家不大也不小的饭店里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很是珍惜这第一份工作。十几天来,他都干得很卖力,老板娘和同事们好像都有点喜欢他了。但是,到了今天晚上,正是饭馆里人多的时候,他不小心滑倒在地,摔碎了五个碗,那个老板娘一生气,也不顾他的苦苦哀求,把他连推带搡地赶到大街上来了。那一刻,他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又流了泪。他感觉自己还不如那老板娘随手扔在马路上的那块破抹布。
他带着恐怖的心情看着陌生的街道。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一种深切的孤独的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痛苦地明白,自己今晚要露宿街头了。幸亏早些时候他在饭店里吃了一碗牛肉面,要不然的话,他还得化钱去买些吃的。他随着人流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着,不知不觉来到了中心广场上。他身心俱疲、悲痛满胸地坐在台阶上,茫然地看着那些无忧无虑的人们跳舞唱歌,心里体味着辛酸和孤独。
在那个饭店里歇都没歇一下,忙了整整一天,他有点累了。他在那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坐了一会儿,觉得腰有些不舒服,看了看四下里,见附近没有人影儿,也不管地上脏不脏,便躺了下来。他仰望着那没有星辰的夜空,依然可以听到广场上轰天响的舞曲,唱歌声,依然可以看见人影在城市那华美的灯光中闪动着。他看着看着,意识渐渐地变得迷迷糊糊的。后来,他睡着了。
他睡得很沉,不知道什么时候广场上已经没有了音乐和歌声,也没有了人群,只剩下街灯的光寂寞地照亮着广场那灰暗的石板地面。他更不知道什么时候风静了下来,下起了雨来。雨顺着风势,急急地扑在他的身上,脸面上,他醒了过来。他连忙转移到了体育馆的廊檐下。
变化多快啊,白天还是个多么热闹的世界,街道上的人和车多得数不清,就像湟水河里的水一样在流。可是现在,仅仅只隔了几个小时,街上的行人不见了,来往的汽车也少得可怜,就连天气也变得又冷又湿。白天里的那些衣着又光鲜又时髦的人们此刻正睡在宽大柔软的床上,盖着温暖的被子,做着香甜的美梦。可是他呢,穿着单薄的衣服蜷在城市建筑物的冰冷的墙壁前,在冷风中瑟瑟的发抖,可怜的情状就和那过往的车辆扔在马路上的饮料瓶差不多。
一阵冷风扑面的吹来,把几滴冰凉的雨点吹到了他的脸上。他吸了一口冷气,把身体蜷缩得更紧了。这彻骨的寒冷让他的睡意完全消失了。他看着雨雾中那带着倦意的昏黄的街灯,它们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向暗夜中散发着一簇簇的光。高大的建筑物的黑影紧紧地挤在一起,使夜色更深更浓。
又是无尽的绵绵的悲痛,又是两行眼泪。他抬起头,模糊的双眼朝东望去,那里依旧是一片黑暗。
“明天会怎样呢?”他幽幽地想。
相关推荐
海南藏绣发挥地域特色 精心打造手工业品牌
海南藏绣巨型广告牌 为进一步营造品牌宣传氛围,扩大青海省著名商标“布绣嘎玛” 影响力,最近由海南州布绣嘎玛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精心谋划、投资、提供,青海省玖玖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制作的20m*6m的大型户外企业形象广吿牌于1月16日在西宁往贵德高速公路...
2013-01-18 编辑:admin 3870青海省海南州2012年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青海省海南州2012年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海南州文联先后2次组织全州书画摄影展,省内外著名书画家笔会2次,全州美术家座谈会1次;州文明办、教育局等八个部门举办了恰卜恰地区“欢庆七一、喜迎十八大、童心向党”歌咏比赛活动;各县和州文化单位开展以“...
2012-09-25 编辑:admin 4517支扎大寺附近发现一处神奇的“卧佛”
最近,一位藏族中学生在支扎大寺补习期间,偶尔发现位于支扎大寺附近的“贡保直亥乃”神山,原来是一个惟妙惟肖的“卧佛”。“卧佛”十分逼真,用肉眼就可以比较清析地看到其轮廓,拍照后更加清晰。 “贡保直亥乃”是当地群众祈求幸福、平安和吉祥的一座...
2008-08-25 编辑:admin 5178“高原脑科学研究中心”在西藏拉萨揭牌成立
“西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高原脑科学研究中心”7月19日在拉萨揭牌,西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纪建洲在活动中表示,高原脑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将为高原居民心理健康的预防与维护提供科学指导,为高海拔对认知功能影响的相关理论以及高海拔脑功能异常的调控提...
2017-07-21 编辑:admin 4125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