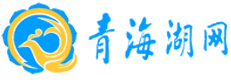邦吉梅朵文学评论作品

邦吉梅朵(1988——),安多宗喀人,又名祁发慧,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目前主要从事少数族裔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评论文章散见于《东京文学》,《牡丹》,《格桑花》、《郑州师范学院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诗歌评论》、《河南作家》等文学刊物与学术期刊。
雪飘,雪落,雪为火
——评阿顿·华多太的诗
邦吉梅朵
作为七零后的阿顿·华多太是第三代藏族汉语诗人中的佼佼者。他的诗歌是一种由“根”发生的写作,所谓“根”必是语言之根、族裔之根、文化之根等多重指涉的综合,甚或笔者感知触角未能涉及的那些隐秘之根。这意味着诗人寻找、发现、感知、认同等一系列活动的亲历亲为,在此意义上,华多太的诗是从经验到的情境开始,从深有感触的片刻开始,记录发生感触的瞬间,记录足够强大的主观感受发生的瞬间。或许正是由于此,华多太多年的写作中一直保持着反思和找寻的姿态,用图博特人未被祛魅的原生的热情抒写自我,抒写雪域以及和我们一并存在着的一切。读华多太开始写作到目前创作的诗歌,能明显的察觉到他不同时期的写作主题、话语方式、风格的流变。基于此,本文将对华多太的诗歌作出整体的观察。
一
诗人写诗的目的,无非深入到事物的内心深处,把自我的内心和事物的内心联系起来,而后寻找到一种与事物之间尽可能完美的对应或吻合,即寻找某一事物所具有最本质的东西或者说最主要的特征,也就是诗人实现自我与世界融合的“中介物”,华多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以来,就找到了贯穿他写作的中介物——雪。雪在高原之外的平原是冬季的特权,在平原之外的沿海是令人新奇的震惊景观,但在青藏高原它再普通不过,雪的自然属性和季节属性在这里被无限扩大,这块土地被先人们称为“雪域”,因而,雪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华多太有这样的描写:“雪很轻/压弯树枝的时候/麻雀飞了/翅膀拍碎雪的花瓣/仰头望云/天是一片荒芜的森林/枯叶都变成了雪/向下飘扬着/那些无奈的羊/在雪坡上/走来/走去(《雪》1993年)” 。松软铺散的雪与麻雀、牛羊一道活现于诗人的笔下,雪成为华多太笔尖流转的阿涅阿斯线球,是他寻找到的事物之源。与雪天然的类似亲缘的关系,使得华多太更容易在缤纷的表象中抓住雪和自己某种细微的层次和关系,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欣慰和轻松,反之,他表现出一种怀疑、困惑、迷茫。
有一天,我突然梦醒于冬季
发觉地上的雪都落在遥远的天空
辨不清雪域往常的容颜
——《雪域》1994年
他似乎清醒的知晓,飘飞的雪花、洁白的大地绝不是他想要表现和书写的,徜徉的牛羊、丰茂的草原也不是他的雪域所特有的。他想表现的雪域应该更为丰富和多彩,更为深厚和斑斓。因此,他竭力试图在自身和自然的共生关系中,寻找到一种对雪更为深刻的理解。在随后五年左右的写作中,他将这种寻找表征为对自我的理解和认识中。尤为明显的是,离乡求学的差异性体验,工作后熟悉而异质性的生活环境,似乎激活了华多太寻找自我的感官和神经。“我开始在暮风中寻找历史……在那堆历史的废墟中/经常置着一盏可怜的佛灯”(《图博史》1995年)。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在血液流动的亲缘性中,华多太找到了那个先天的自我——图博特之子、雪域之子,这意味着精神的皈依和文化认同的确立,可是认知的历程是曲折而痛苦的。他一度陷入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不能自已,甚至要终结自己的写作:
再见了,荒诞缭绕的转瞬人生
从此我将不再杂草中充当鲜花的角色
我确信消失的过程不会像诞生那么完美
但决定不再作诗了 阿秉达
——《感谢天葬》1996年
此时华多太的情感是饱满的,激越的,但是不确切的集体信仰的认同,让他感受到了灵魂个体化无可慰藉的孤独。他不惜用“天葬”的形式解构一个已然存在的“我”,而后建构另一个理想的“我”。与其说“阿秉达,我决定不再作诗”是诗人告别自我的一种方式,毋宁说他是在用冲撞的方式形成并强化自我。自我建构从来不是特殊的孤单的个体生活,必须参与普遍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在此意义上,华多太对自我的建构是积极的,主动的。他选用“天葬”这一藏民族独有的仪式,欲念通过这种集体的经验,寻求确切的族群归属感。一声阿秉达,一句“在高原的声乐里我仍旧撞到雪域的脉搏”,使他意识中模糊的焦虑逐渐清晰。他这样写道:
我是一位在汉语里呼风唤雨的藏人
蹲坐在离骚的旁边给自己缝补皮袄
让布达拉在拥挤的汉字里高高擎起
于石碑的中央感受局外的温暖阳光
——《我是藏人》1998年
《离骚》与《格萨尔王传》、布衣褂子与羊皮袄所表征的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以及两种传统让华多太陷入一种纠结的沉思之中,然而最让他焦心的恐怕是关于当下的表述,为此他发出这样的慨叹“自己的诗——发自灵魂的谚语,曾经不为母语所铸而感叹惆怅,……,我向她请求原谅。”此时身份认同的焦虑外化为能否使用母语言说和表达,“民族属性和文化认同的尴尬通常会发生再处于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人们身上,尤其是当母语身份处于弱势的历史关系之中。” 经验构筑的自我肯定是不断服从的,华多太在服从中平衡着这种尴尬和焦虑,直至女儿的降生,他强烈的自我情绪才得到缓冲。
月儿圆时 我想起曾经朝归拉萨的路途
……
从此我常常梦见女儿的诞生
……
我的女儿呱呱坠地 宛若清晨含露的鲜花
……
我感谢遥远的菩提迦耶给了我生命之续
……
仿佛是佛陀身后辉煌而温馨的光环
……
护佑着我的感觉和女儿洪亮的叫声
……
等待着女儿和我蔚蓝的祝福
——《月圆的思绪——献给女儿娜木措秀姆》1998
这首诗中,所有的物象和隐喻都是积极的,“鲜花”、“光环”、“祝福”无一不把诗人包裹在暖暖的幸福与喜悦之中。女儿的出生让华多太获得一种生命的连续感,而生命的连续感正是一个人完成自我认同与生活认同的必要前提,生命需要重复。因为“重复以某种方式包含着经验,重复是人向自己并向他们再现身份的框架,重复是一种纯形式意义上构想的回归” 。一个人脱离母体意味着脱离一元体,变成外在的主体,因此孩子是“对象化”的人,孩子和父母构成共生关系。在此意义上,女儿是华多太镜中的自我,是他自我的他者化。这无疑为诗人寻求自我的、族群的、文化的认同提供了途径,那种焦灼的情感不再复现,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父爱和一份从容,一份希望。
初为人父的华多太,在寻找自我的神秘感受和经验中,觅到他与雪,与雪域之间特殊的关系——雪的谐音——血,血缘,血脉,血脉之根。组诗《十四行》、《雪域组合》及《自画像》、《诗人的诗》等诗篇尤为明显的表现出诗人对生命和人生价值、意义和个人情感世界的集中探讨,从自我认同的身份焦虑中透露出自觉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
二
不知华多太何因何故搁浅写作近十年之久。2004年诗人伊丹才让的溘然长逝激活了他写作的动力细胞,抑或“抑制不住对先生的怀念,纵然执笔一诗《诗人伊老》宣泄敬仰之情”。这是他停笔十年之间唯一一首诗作:
你也曾经在阿妈的挤奶声里长大
一同羔羊采撷彩云里的童年
如今已是桑烟里升起的故事
缭绕在雪域家族的上空
那悠悠飘逸的诗歌 在高原的风中
馥香淡淡 令人心旷神怡
面对前辈诗人的逝世,华多太的心情是悲怆而沉重的,但是生长在雪域和草原的族裔诗人们,切身经验者某种时间和空间的敏感性和无限性。即使伊老不在雪域,他留下的诗篇依然萦绕在年轻诗人的脑海,回响在雪域家族的上空,甚至在飘飞的雪花中,有伊老在《雪域》留下的《晶亮的种子》 ;即使伊老不在草原,草尖上依然跳跃着传诵的词语,摇曳在草原的酥油灯依然长明。在同为族裔诗人的伊丹才让和华多太在诗歌创作上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对话,作为第三代藏族汉语诗人,华多太的写作是对前辈诗人的续完和对偶,他需要在影响的焦虑中完成前辈诗人未能完成的诗作,需要在与其他强者诗人的竞技中找到属于自己诗歌的话语方式。可是终结前辈诗人的影响绝非易事,或许是为了打碎前辈诗人对自己诗歌造成的连续性的影响,华多太在《诗人伊老》之后再次停笔。而这篇诗作对他到目前为止的诗歌创作而言,是不可忽视,不可不察的。放弃或者坚持,搁浅或者继续是一个诗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取向、不同选择、不同思考的表征。
倘若对华多太现有的诗歌做一个阶段性划分,那么可以以2004年作为风水岭。2004年之前的诗作,犹如空中漫天飘飞的雪花,飞扬流转,牵引出一个文学青年的爱欲情仇、苦难忧郁、迷茫彷徨;蔓延在情思、诗思的虚幻原野,降落或者堆积;在诸多的变数和重复中,用单一的色调淹没了错落纵横的景致;致使诗人无法承受飘雪之轻带来的沉重而搁浅更多的诗与思。2004年之后的诗作,犹如即将落地的雪花,承载着独有的生命形式,在落停的瞬间摆出坚定的姿态,用单一的颜色隐藏一切斑斓,用恒定的温度摆出了一位族裔诗人特有的姿态。《诗人伊老》恰是一种沉稳的承前启后, 总体而言,他的诗歌既是返回、向内和回溯性的,同时又是敞开、真实、担当与介入的;他的诗歌的内核始终是一种多元化和异质化的身份认同。
[FS:PAGE]
三
十年之后再次提笔时,华多太的诗歌走向对现实的干预与担当。尽管当下的现实或许确如诗人奥登所言,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对我们当今时代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各种苦难和困境,诗歌确实不能也无法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但是诗人的可贵之处或许恰恰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他要把引起他心灵触动的被我们有意或者无意因脏的东西勇敢地说出来,他要揭开以各种名义覆盖在事实真相上的那层幕纱,把真实的处境揭示出来,他要用诗句做一种提醒,一种“科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重温诗歌华梦时,华多太携带学者身份进入诗歌 ,思考藏民族的历史和命运,表现对族裔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传达出忧患的幽思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敬仰,他写下《再见,德令哈》、《玉树,别为我哭泣》、《区别的人》、《青海湖,请原谅我》、《雪在高原》等情感饱满的诗篇,不可不察的是他重写了《我是藏人》(2009年):
我从达尔文晚于罗刹女的婚礼
和这个初为大海,后为森林
再为草原的沧桑传说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我从发光的三十个字母
在世界最高处的上空
星星般闪烁的格言绝句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我从格萨尔的赤兔马赛过
阿喀琉斯的战马,与特洛伊战争
同样经典的霍岭大战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我从彩超般的藏医胚胎图
释解生命本质的藏秘
和算得出月亮上有水的历法里
感觉到自己
是个藏人
这首诗长达17节,诗人用“我从……感觉到/自己是个藏人”的句式,讲述着族裔历史,族裔文化。相比较十一年前那首《我是藏人》,这首诗中他的情感是理性的,态度是客观中肯的。“我是藏人”的肯定陈述不是狭隘的族群意识、族群认同,而是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或根的意识,是一种对特定的场所、人物谱系及其历史踪迹的意识,是对特有的生活习俗,具体的地方性的人物与事物的自我叙述。他意识到自身不只存在于一种普遍历史而是为一种独有的文化传统所造就。从这些话语中,能够清晰地感知作为族群一员独特的历史、宗教和习俗背景。一个人在一种独特的背景下才会被认知,人们之间的交流也意味着不同背景的相互确认。对华多太来说,藏族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族群归属,它意味着承认个人与一个地方,一种历史世界之间更为深远的联系,获取族群的过去及其历史记忆,是精神不朽感的源泉。
相对于日趋同质化的生活景观和体验,华多太的诗歌就是他自己对族裔历史、文化、现实、情感、体验、精神、理念的翻译。或者说,他试图用诗歌作这样一种努力和提醒:作为个体,不能无视历史和集体的维度,不能隔断个人与民族的历史记忆联系,就像不能隔断族群名誉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一样。他深切的感知到如果没有集体记忆,族群身份与特性就是一个空洞的事物。没有记忆,生活就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机械的重复。即使是曾经的罪恶与苦难,也必须是靠记忆的功能来净化的。也是从2004年之后,华多太对自我(self)的寻找和认同开始转向对主体(subject)的辨识和认同,主体性作为一种对自我身份和各种能力的认同,是他在重返诗歌舞台之后集中力量积极追求的目标,重写(亦或是翻新?)《我是藏人》就是华多太对写作主体进行持续反思和探索的表现。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安多大地》(2010年):
安钦岗嘉以东的山河,多拉让姆以西的草原
安多大地,像高原的胸膛挺护着雪域的心脏
……
在卫藏赞普为佛法的去留付出帝国的代价起
吐蕃犹如一支古老的羌笛,遗弃在世界屋脊
……
在被称为叶毛唐的风景里播下了王室的种子
使松赞干布的基因继续在安多的血液里流淌
读这样的文字会时不时地感受到一团热情裹着骄傲从文字的缝隙中扑滚出来,如携带着热力和水珠的蒸汽无可抵挡地从毛孔氤氲到皮肤的深处在身体的曲折出浸润熨烫,他的叙说是那样的明晰和真实,安多大地是华多太内心空间维度的象征,是时间、经历、记忆的容器;是他地理学意义的情感空间。过去、现在、未来都在那里凝聚,这是华多太个人的,也是属于族群的,文化的。熟悉民族史诗的人,很容易从这些词句中读出史诗的规模和形式,华多太用前辈们的讲述方式向今人传递着看似古老的信息,但这是他诗歌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品质,他对族群的认同、精神上的渴望和情感上的怀念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是来自对故土显示性特性的观察,将一己之情融入到历史的脉络和对其他族群的参考和关照之中。相对于当下其他族裔诗人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的追求和实践而言,华多太是老派诗人了,可以戏称他为“古典诗人”。他的诗歌既没有先锋的姿态也没有智性光辉的绚烂,但这似乎不影响他用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传递对雪域平常事物的重写与自身生命悸动的品味和摩挲,他如此写到:
在城市中心,你也许
把不到高原脆弱的脉搏
因为你距雪的呻吟
相去甚远。
我多么向往一双石头的翅膀
逆时飞翔,敲碎汽烟的头盖
打断污流的筋骨
畅通无阻地
雁领蓝天和白云
为雪山还原正义,为河源
输送永恒
在逐年贫雪的冬季
向往水草
永恒的光芒
——《轮回:远去的雪》2008
华多太似乎从“远去的雪”中窥测到整个大地的命运,窥测到整个人类的命运,他表现出一种担忧的状态,不惜用“敲碎”、“打断”加以暴力的干涉,或许在浪漫的族裔特性的影响下他是理想主义的、乐观向上的,他相信有一束“永恒的光芒“护佑雪域。在藏民族的生活中,光不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现象,它更多的与宗教、神话、美联系在一起,光在藏民族每一位个体的心中神圣而神秘,他们赋予它独特的象征和意蕴。在族裔文化内在的影响和熏陶下,华多太的诗歌中也不乏对光的描写:“我跏趺与塔尔寺的菩提树下/点一盏普天通明的佛灯/为那些黑暗和恐惧中沉睡的孩子/送去光亮,送去童真”(《玉树,别为我哭泣 》2010年),“六字真言的光辉,从雪域/曝亮那些已故的/和极度悲伤的黑暗角落/顿悟生命的无常”(《 远去吧,萨达嘎波——为汶川大地震》2008年)。诚然,他笔下的光是酥油灯、长明灯的转写,甚者,我相信出于对雪的偏爱,他笔下的雪也闪着金光和银辉。
瓦尔特?本雅明把光(aura)看作是世界的诗意之所在,自然中任何物质形态都散发着灵光,灵韵是人类免遭现代性重复、复制、异化的保护层,是一切生命与人与世界具有的神性底座,构成我们关于全部环境的诗意,诗意寻找光,光是大地,是气韵,是人之生命为之呼吸的一切养料。而现代性是一个机械的、工具性的技术,机械的一定是复制的,复制对灵韵造成伤害,灵韵的丧失消解了我们生存所依据的本真性,使我们的心灵被损伤为碎片状态。可是雪域高原无法阻挡现代性普遍发生的浪潮,华多太用诗人的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
请不要让突兀的囱烟
紊乱我真诚的体脉,不要让烟囱
落下的影子,挡住
我的视线
请不要让饥饿的市侩
挤压我清纯的声音,不要让市侩
投下的影子,挡住
我的视线
——《请不要挡住我的视线》2010年
华多太站在本土、本民族与现代性发生的交叉点上,怀着忧虑,发出呼喊,摆出姿态——请不要挡住我的视线。诚然,此处的“视线”是对当下人类普遍生活、生存状态的抽绎。行走在高原,看着一辆辆金旋风半挂货车满载矿石、煤炭离开,留下呛鼻的尾气;看着原本熟悉的草原因架起蜘蛛网般的高压电线而变得陌生;看着野驴、黄羊惊恐的眼神;看着逐年上升的雪线……那种感触是复杂的,难于表述的。华多太亲历着高原的每一丝变化,最让他心痛的莫过于自己心中的雪域圣地被动的面对和接受着现代性的侵蚀,甚至沮丧于无力抚慰被挖掘机、钻井机蹂躏过的高原大地,懊恼于看着那些交不上名字的铁疙瘩挺进高原而自己势单力薄无能为力。在此意义上,我开始明白为何这个使用智能手机、能熟练操作电脑的现代诗人为何有着那么深那么重的古典情怀怀,为何他的诗歌隐含一种回望的美学。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自我的寻找和自我的认同。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说:“怀旧是人寻求保护、抵御危险的一种本能,是在预期未来时对过去的重构,是一种与时间保持对话的策略。” 但是最让诗人怀念的恐怕不是或徜徉于草原,或念经礼佛的传统牧民生活和宗教仪式生活,而是用母语言说的渴望:
我确信我的母语,不会变作陶罐
也不可能拘泥于墙上,成为后来人的追忆
我离不开这个高高的家园,离不开
岗坚和咔哇坚这个独一无二的古老标签
……
我也常在高高的山坡,煨祭山水之神
双手合十在头顶,五体投地
痛用精美的母语,穆诵大山的形体
——《请不要挡住我的视线》2010年
其实,就某种角度而言,华多太无疑是幸福的,他可以自由的游弋于母语和汉语之间,用母语写学术论文,用汉语写诗歌,在伸手的瞬间抓住“两个世界”。更何况,他的诗句中时常会留下母语的痕迹亦或母语的思维,每每情感强烈时,情绪集中处,总会流出母语的汉字译音。恰如诗人自己所言:“我始终在用自己的个性演绎汉语,在异语中留下一些母语的烙印,乃至母族优良文化的众多元素”。
四
诗歌写作如何只沉湎于自我、一己情怀,往下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窄,而如果把大地、万物与生活作为根基,用灵魂与生命去体察,诗路也许会越来越宽,越来越远,因为万物是真理的寓所,对万物的热爱与演说是对生命尊严敬畏的表达。日常是生存的本相,对日常生活的进入与剖解是诗人对诗歌伦理的一种主动承担。诗歌是个体经验的独特表达,它有唯一性,是个体瞬间灵光的闪现,是不可复制的,诗歌可以用不可复制的本真性构成现代性中的一种文化抵抗,在灵韵消失的时候,抢救灵韵,恢复人性的光辉。诗歌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于造就时代精神,提供时代所最缺乏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我不会华多太十年的搁笔而感到遗憾与惋惜,这十年的沉淀,让他体悟到了一个诗人,一个族裔诗人真正的使命。萧开愚先生在一首《原则》中这样写道:“诗人的责任至今没有终止/给一些人勇气/给一些人唱安魂曲/这样的诗歌/符合大家的境遇。” 可以看到,作为族裔知识精英的华多太,察觉了已经出现和可以预见的问题,承担了一个诗人一个学者能够承担的责任。
诗人张曙光有过这样的表述:世界上只有少数几样永恒的东西,石头和雪——长久的和短暂的。对于华多太来说,石头是他的生命之根,是他的家乡安多道帷——石头帐篷之意;雪是他诗歌经验的集合——《忧郁的雪》和《雪落的声音》。确实,雪这个最古老的原型意象,如幽灵一般环绕于他的诗歌生涯,他亦或每一个雪域之子,都绕不开的圣地之雪,高原之雪,那个称之为雪域的地方,是千万图博特子孙生长环境的转喻,亦扎根于华多太的血脉与骨肉之中,快乐与悲伤之中。雪是沉寂的,凝固的,需要借助热的促动作用才能由冷与白的静默转化为温与明的飞扬。华多太用了十年时间去寻找这股暖流,铸雪为火——发出真正的声音,写下真诚的句子。无意去明辨石头帐篷的坚固是否带给华多太一份坚定与执着;无意去揣摩再次起笔的文字是他灵魂痛苦的镇静剂?是烈日中的一阵微风?是沙漠中的一滴甘露?还是一个解决自我根本的决心?一种来世生命深处的勇气?我能做的只有倾听,倾听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思想,继而寻找,寻找一种回响、一种震颤、一种力量。
[FS:PAGE]
云下巴塘,风中玉树
邦吉梅朵
当延误的航班滑行在巴塘机场时,全是静默的延长符号,太阳挤干了它所有的热能与焰质,懒懒地滑下去,贴在匆匆下机的人群中,有锋无芒的阳光封住意欲感叹的双唇,怎奈蓝天白云、绿草清水葬在眼中不能动弹。终于,在呼吸的抖动中得到提示——这是玉树或者结古朵。本以为,世界是均质的纯客观,自打双脚落在巴塘,就看到一处幽兰光辉而神圣的空间向我敞开,我想朝着它的四面八方奔涌而去,拾起关于它的每一个微尘微粒。
玉树,没有庞大的固体建筑伸向高空,冷漠地环视各种像膏药一样的楼顶;玉树,没有被黑暗卡住的脖子,嘟嘟囔囔自言自语;玉树,没有层层叠叠的沙粒之光让你透不过气来,如流沙堵住你的毛孔。玉树,经过了千百年的聚集,堆满了人与物;玉树,无数头颅在广延空间里发出笑声,在新与旧的结合中构成一种当代存在;玉树,结古寺的塔尖慢慢往下坠,落在格萨尔王气宇轩昂的雕像上,凝成一股浩然之气,伴同无言的暮色幻化为当代山头一种明亮的质地;玉树,嘴唇与喉结慢慢地提示——贴近自然的地方。
第一眼玉树,与自然相关;第一声结古朵,与诗歌关联。
自然的玉树,在永不停息地改变别的事物,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诗歌的玉树,是一种向上的力量,在成功举办“2012中国?玉树唐蕃古道诗歌节”之后,携手诗刊社,举办“‘玉树?青春回眸’诗会暨第二届中国?玉树唐蕃古道诗歌节”;文化的玉树,是格曲河、勒巴沟、赛巴寺、嘉那玛尼、文成公主庙、通天河环绕的美丽康巴。
自然与诗,上天下地,牢笼百态,一切都浑然为整体,彼此聚集,彼此组合。《嘉那玛尼的星空》下,古老的族群在《阿妈的青稞地》上谱写《创世纪》的诗篇《格萨尔》;《玉树有多远》?遥远而恒久的疑问,一条《路》连同《一条顺流而下的河》,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绎着《古道风韵》;回首《友谊之桥》,多想《纪念》一下《仁增仓央嘉措》,或许他此刻正在拨动手中的念珠口诵《般若六度》;今天我们左手携《三江源之恋》右手带《唐蕃之恋》,在巴塘《草原抒情》,祝福我们共同的《家园》——玉树。(注:书名号之内文字皆为“‘玉树?青春回眸’诗会暨第二届中国?玉树唐蕃古道诗歌节”所朗诵的诗歌篇名)
我不知道人在自然中到底能掌握什么,但我清楚语言能把自然的声音、香息、色彩布满我们所有的器官。在玉树二中,遭遇多位激情澎湃的母语诗人,他们的朗诵用焦灼的热情、沉厚的力量将我钉在座椅上不能自持,特别是那软腭鼻音的共鸣与回音,调动我所有的知觉去捕捉母语走过的所有事物的纹路,以及在细线密纹里刻下的踪迹。想象母语的音节携带色彩,把各种颜色撒在事物之间,还有母语复杂的音变把它染在事物的肢体上,事物会散发各种各样的气味,点滴入怀地把那些香透了的味道传输、搬送,披肝沥胆地融入你的毛孔,迎着阳光,你看那纤纤细细的汗毛上有流动的三十个字母和四个元音,它们在自然的空隙里运行组合。我似乎憧憬到一种攒集的温暖,它真实而安全,淳善而可靠。师父说,任何声音状态都要归结到意义,这有义无形的声音,传递所有事物的密码,包括康巴大地久远的历史,这有形无义的声音,分辨你血脉中的蹑踪收迹。
一阵风轻轻吹过,游丝如悬,我真切的感觉事物从身边穿过,留下屐痕处处,一枝响箭穿过我头颅思维的丛林,射落时间的碎片,不断把梦想挤压,一个空间连着一个空间,是什么在流淌,伸手捏一把,感觉到掌中细密的纹路里所有物质雪片一般融化,随手势观望,全部是自由的精灵凌空飞翔。有什么在人与自然间涌动,或者接受自然的馈赠?词语的排列,语汇的组合,构成一种重大的发生——诗歌,意义生成的振动过后,包容了无和有,包容了自然之外更大的自然。诗歌如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人能把诗歌写完说尽,诗歌或许仅是对自然的美丽展示。
还是在玉树二中,有一个题目叫《藏族文学:来自喜马拉雅的叙述和诗章》,这样的题目对场景、情节都有要求,所有的发生都是从题目开始,自然也逃不掉诗歌的逻辑和自然的思想。文学永远不是一个固定的所指,它是具体事物最真实的灵魂,有如蜻蜓透明的翅翼拍落花丛的奇香;浩渺无穷的星空,所有事物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呈现,我知道强行拼贴出的看法总是不那么可靠,语言上的发生对实际生活的发生而言,总是有一段不清不楚的距离。索性用语言开始一种思维,省去掠耳而过的空声。所有的词语都从声音中顺延,固定为某一符号的象征,成为我心灵的表述。
大概是热闹过后的午夜,梦见自己去了一个陌生的高原,在岩石上攀爬,无可凭依,随时都可能摔得粉碎,惊得我裹紧了被角,睡去是一片梦,有族人嘹亮的歌声和欢快的舞姿,醒来却是一片空白。离开的早晨,结古朵的阳光一点也不灿烂,我的内心布满了忧伤与孤寂。我想,人到底在和什么东西诀别?去机场的路上,不停回望结古寺的方向,一种地方感,一种地方信念,一种文化联系和情感纽带;不断回拨手机中的照片,一条切近的路,却标示了那么多记忆的符号,收拢黑暗的羽翼,匆匆赶路,徒增感伤的回忆。
[FS:PAGE]
把故乡的还给故乡
邦吉梅朵
在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物质和文化的过度消费,导致诗歌不可避免的走向凋零和庸俗,呈现出数量居高不下和质量不经推敲的显性矛盾。写诗的人很多,但能够写出高质量诗歌的人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信仰缺失是根本。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对故乡的热爱,或者已经失去了故乡、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的内核自然轻浮而庸俗。活跃在青藏、川藏高原的一批族裔诗歌群,却固守着原乡的精气神,在热土与宗教气息中感受生命的点滴过往,组合成独有的一种诗歌现象。其中,玉树诗歌群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我一直坚定的认为,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少数族裔诗歌群体或许会提供一种契机。
一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玉树藏语意为“遗址”。地理位置大致介于东经89°27′~97°39′,北纬31°45′~36°10′,北与本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相连,西北角与新疆的巴音郭楞自治州接壤,东与本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互通,东南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毗邻,西南与西藏昌都专区和那曲专区交界。多元文化交汇,即保存着康巴文化血脉,又浸染着安多、卫藏和维族文化的具像符号,促使玉树文化丰富而形象,栖居在这里的族裔诗人们承继着原乡故地的情思,不断摸索着现代诗歌前进的方向。
玉树诗歌群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在原乡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同时,不约而同的用轻巧和庄重并存的方式努力实现着诗歌的环境与经验的维度重合。朱玉华的《一户人家?一座寺》里,他用光线和映象传递着某种记忆中的信息。
还记得吗?那时候这里没有山
满坡的荒草,住着一户人家
冬窝子里的羊粪蛋儿攒堆等着归来的人儿
放羊小伙身旁采蘑菇的姑娘,洁白的牙齿闪着太阳的光
一曲牧歌,朝着爱情的方向
喇嘛择的日子里,奶茶喷香
黝黑的脸庞笑成花的模样
傍晚的夕阳,喜气洋洋
他把原乡的记忆分解成为一些细小的可以触摸到的事物,比如荒草、羊粪蛋儿、牙齿、阳光、奶茶、喜气洋洋的夕阳等等,它们活动于诗人的感情与理智之间,活动于视觉与声音之间。这些细小的事物互相促进,慢慢的将诗人的原乡记忆勾勒完整。诗人花了大量笔墨罗列记忆中熟悉的意象,最后,把记忆的肖像回归到一堵许愿墙上,这恰恰是诗人最高明的地方。他用一连串罗列的形象,呈现出外部世界之美,同时,这些形象那么实在,那么缓慢,那么精确,他把最抽象的智力活动赋予了具体形态,强化了秩序,从而导引出诗人对于原乡的朴实笔触。换言之,可以理解为从俗世生活走向自然环境的一种追求和对自然环境于人的一种积极思索。
过去的耳朵倾听从前的回忆——
还记得吗?那时候酥油茶必须配着糌粑
暗红的土墙,要等来年再刷
秋末霜打过的植物,收割进帐房
整齐码放在师傅的门前
诵经声中晾干,研磨,搅拌
绛红色的袈裟没有袖子,染两条红色的胳膊,嬉笑着取暖
四月的雨夹雪,土墙像没有吃饱的孩子
大口吸吮暗红的颜料
焕然一新的经堂,师傅端一碗酥油茶,细嚼慢咽一块糌粑
于诗人而言,记忆中的那户人家是贫穷的,也是欢喜的,那座寺庙是古老的,也是崭新的。他试图还原一种真实存在,用大量的描写将情感与思索深深隐藏起来,让读者看到一幅画,沧桑庄重而不失活泼灵动。他的世界的秘密便隐藏在文字符号的各种组合之中,形成一种可以认识或者解读的模式。从这种典范式的模式中,清楚的交待出个体于原乡的记忆深处强大的原乡情感支撑。
同样以记忆模式书写原乡的还有魏彦烈。《遥望故乡》里,他写道:
如果不是远山的阻拦
顺着草原望过去
那片玉米地一定还在
梨树已经挂果
几堵站不稳脚跟的土墙
圈养着一间老屋
敲开生锈
对于诗人而言,对于故乡的记忆是一种概念转换,他是将玉树作为支点,对自己精神的原乡进行一种回望,他的原乡在别处,但玉树却给了诗人走向原乡的一种方向。因为玉树的存在,他才最接近原乡的情感,才最接近积淀和抒发。他通过记忆中的画面描述出一片玉米地和几堵站不稳脚跟的土墙,还有老屋和生绣的门环。应该说,诗人的原乡应该是这种模样,但不是,诗人的原乡应该是站在玉树看到的这般模样。安静而古老的想像。在他另一首作品《画一轮圆月》中,也出现了村庄和玉米地。
在可可西里点一盏酥油灯
画一轮圆月,让风打着
我会叮嘱一条捷径
留下一个村庄的名字
穿过玉米地的小路
需拐过几个弯
拔一把青草
就坐在池塘边
两首诗歌,都是以玉树为破题点,远山、草原、可可西里、酥油灯,这些专属于高原的形象符号被诗人用于挖掘原乡记忆的支撑点。从另一个角度看,诗人提供了一条线索,是在原乡上生长还是在他乡为原乡生长?物件易主决定了诗人作品中许多情感和人物的相互关系,即原乡即是诗歌起点。
[FS:PAGE]
二
在我的意识中,个人对故乡是带着使命的。只有对原乡有勇于担当的使命,才有可能将故乡的一切写得更加鲜活具体和深刻。在玉树诗歌群里,才仁当智、秋加才仁、尕松旦周、白玛文青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将个体于原乡的情感和担当完整的体现了出来。同时,他们的诗歌里都带有浓烈的宗教气息,这也是族裔诗人无法被模仿的特质之一。
才仁当智的《三年分离——写给儿子》中,他相信生命的诞生源于上天的恩赐。
一声哭泣
宣布一个生命的开始
儿子
你以天使的名义,来到了人世间
…………
在他的另一首诗《青葱岁月》里,也能找到神性对于他创作导向的引导和影响。
不老的神话已经风化
转山的人看到
青春只是二十年前的一匹白马
佛学倡导慈悲和智慧,而这也成为族裔诗人与生俱来的诗歌灵性,他们的诗歌存活在浓烈的宗教气息中,带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和对自然无限的歌咏和幽思寄托。于是构成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会延长、迂回,但都是对诗歌连续性的一种自然加工,因此,他们的诗歌更趋向于一种接近自然环境、接近神性的经验加工。他们借助神性,在原乡之中努力寻找更准确、更形象、更生动的原乡。比如秋加才仁的《巴颜喀拉海拔的传奇》:
从云层中飘落的风
极地的寒风
在青色的岩石
绽放出牦牛呼吸的文明
触动众神的心灵之笔
一个属于格萨尔的土地
孕育康巴母亲河的源头
雅砻江以婴儿的姿势
承受着牧人的呵护
散落远古的血液
湖泊 想象的延伸
通过顺时针的方向
把敬畏献给了众水
空气稀缺的高原
灵魂在呼吸间
于自然众生同在
诗人相信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相信自己的故乡是一种神性的原乡,一切情感和财富都是神性的赐予。这种简单的想像让诗人把原乡想像成众神庇护下的婴儿,用一种极尽虔诚的方式将平等与爱给予自然和有情众生。换言之,族裔诗人的爱是建立在自然环境之上的,是脱离了小我情爱的,这也是族裔诗人无意识交待的原乡本真内核。在白玛文青的诗歌《信仰的金字塔》,这一点体现得尤其直接和形象。
转经道上
弥漫信仰的空气
拌着煨桑的柏香
朝圣者的身影
像活佛手中的念珠
精诚航行
寻找飞翔的脉络
清洁灵魂的尘埃
每个人的脸上
满载着收获的帐本
……
贴近六字真言的暖胸
仿佛能听到
血管里吟唱的经卷
仿佛能看到
浩瀚中无数的珍藏
仿佛能触到
洒向彼岸的甘露
每一块石头
雕刻了生命的誓言
承载着天堂的阶梯
诗人用藏族独有的行为符号累加渐进诗歌节奏,如真的表达了藏人对于自然、对于生命、对于爱的神性认知和习惯,即个体世界的建立永远在自然之下,同时又和自然及神性融为一体,相互交织,互相作用。他们(包括诗人)相信,每一块石头、每一股水流、每一分空气里都居住着神明,慈悲和智慧的内核贯穿诗歌,贯穿着族裔诗人一生,这也是他们为何将笔触着力点放置于此的根本了。当然,即使在书写小我情爱之时,也是建立在原乡自然与原乡神性的基础之上。如尕松旦周的《伸出梦外的手》:
当你走过黑夜的迷离
淌过自己的障栏
圣水的洗礼之后
在风雨中伫立的
依然是你的骄傲吗
如果
离合 苦乐
顺从与背离
皆为一种缘
在圣水洗涤的生命认知里,诗人相信万法随缘,缘来缘去本是自然,不强求不刻意,这也是高原物质之一。总体而言,族裔诗人在创作诗歌时,通常会不自觉的背靠原乡,以宗教神性作为诗歌支撑,去认识原乡,解析原乡,在原乡之中寻找原乡。
三
在玉树诗歌群里,女性诗人的作用不容忽视。她们一方面延续了神性导引,另一方面又用女性独有的细腻将原乡变得轻巧而迷人。那萨的《美丽世界的孤儿》中,她有意无意的带出一些具象的神性符号。同时又将原乡的情思变得轻而又轻。
傍晚
手里的念珠转完108颗
天亮了
剩下陈旧的空金瓦殿
一只乌鸦
突然失语
在《光的距离》里,用缥缈的感觉去书写原乡情感的模式呈现得更加细致。
双目回归的刹那
光线就那么深深地抛光
折射在暗角的亮点
把帘子拉上
也就扣上了
一面世界
她把自己抛到俗世生活中,用俗世生活的眼光去审视带着神性的土地,这个时候,她的情感世界也是细微的世界。她一方面被细小的俗世世界包围,另一方面又试图运用原乡经验打开神性世界,她有意识的将距离加工成自己于情感、于原乡热土无意识影响的文字符号,以柔情的书写方式把自己对原乡的情思还原得细腻而浪漫。
总的说来,玉树诗歌群以原乡神性为依托,驻足原乡将诗歌本体建筑引向自然和上苍,赋予诗歌本身一种神性和鲜活的力量。
林芝生态旅游增长快效益好
夏季的“西藏江南”如诗如画,游人如织。近日,林芝地区旅游局局长王军告诉记者,今年,林芝地区立足本地优势,扩大目标,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纵深拓展客源市场,生态旅游呈现出增长快、效益好、行业稳的良好发展态势。1至6月,林芝地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2万人次,同比增长...
2010-08-17 编辑:admin 10131“高原美丽乡村”我的家
“高原美丽乡村”我的家 ——共和县高原美丽乡村建设掠影 共和县铁盖乡托勒台村村民吉学花在新盖的六间大瓦房在打扫卫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圆了新房梦……该村的...
2014-07-09 编辑:admin 6274藏研中心与藏大共建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近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大学双方领导齐聚藏大,为合作共建“西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行签字与揭牌仪式,标志着西藏第一家以西藏社会发展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正式成立。 旦增伦珠研究员(左)与西藏大学科研处处长丁玲辉(右)在协议上签字 签字与...
2011-10-09 编辑:admin 3707电影《老狗》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
万导与现场观众进行亲密交流 日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携电影《老狗》亮相美国纽约。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电影《老狗》并与亲临现场的观众进行亲密交流。 据悉,《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给予万玛才旦和他的电影作品《老狗》很高的评价。 ...
2013-05-18 编辑:admin 3293联系电话:0974-8512858
投稿邮箱:amdotibet@126.com